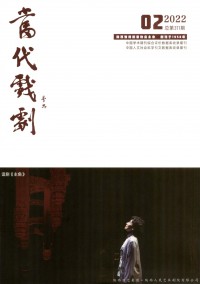當代科學技術(shù)范文精選
前言:在撰寫當代科學技術(shù)的過程中,我們可以學習和借鑒他人的優(yōu)秀作品,小編整理了5篇優(yōu)秀范文,希望能夠為您的寫作提供參考和借鑒。
科學技術(shù)政治學管理
【摘要題】本文評述“西方馬克思主義”關(guān)于科學技術(shù)的政治效應理論特別是法蘭克福學派關(guān)于當代科學技術(shù)是一種新控制形式的觀點。作者指出,盡管“西方馬克思主義”的這種理論存在種種不足,但是他們較深入地探討了當代科學技術(shù)與政治之間的相互關(guān)系問題,提出一種獨特的科學技術(shù)政治學的理論,這對于我們?nèi)嬲J識當代科學技術(shù)與政治的關(guān)系,充分發(fā)揮科學技術(shù)的正面政治作用,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關(guān)鍵詞】西方馬克思主義科學技術(shù)政治效應
【正文】
科學技術(shù)與政治之間的關(guān)系,尤其是科學技術(shù)的政治效應問題是科學技術(shù)觀的一個重要方面。在國外,圍繞科學技術(shù)與政治的關(guān)系問題的研究,已形成了一門新學科,即科學技術(shù)政治學。“西方馬克思主義”特別是法蘭克福學派較早注意到這個問題,他們著力研究當代科學技術(shù)的消極政治效應方面,提出了一個獨特而有影響的觀點,即當代的科學技術(shù)取代了傳統(tǒng)的政治恐怖手段而變成一種新的統(tǒng)治或控制形式。下面我們將評述“西方馬克思主義”特別是法蘭克福學派的這方面觀點。
青年盧卡奇在《歷史和階級意識》一書中已經(jīng)涉及科學技術(shù)的社會政治效應問題。他認為,當科學認識的觀念被應用于自然時,它只是推動科學的進步,當它被應用于社會時,它反轉(zhuǎn)過來成為資產(chǎn)階級的思想武器,[1]現(xiàn)代科學越發(fā)展、越復雜,它的方法對自然理解得越好,就離人本身越遠,越成為片面的、封閉的、與人無關(guān)的東西。技術(shù)的情形也一樣,“技術(shù)的專門化破壞了整體的形象”,“它把現(xiàn)實世界撕成碎片,使整個世界的夢幻煙消云散”。[2]盧卡奇實際上把科學技術(shù)當作物化的形式來加以批判,認為資產(chǎn)階級一方面將科學技術(shù)當作征服和控制自然的工具,另一方面又將它們變成人對人統(tǒng)治的有效手段;科學技術(shù)成了資產(chǎn)階級的幫兇,在資本主義社會,科學技術(shù)越發(fā)展,工人受剝削受壓迫就越厲害,科學技術(shù)是資本主義社會中種種矛盾異化現(xiàn)象的一個禍根。在這里,盧卡奇顯然注意到了資產(chǎn)階級將科學技術(shù)變成統(tǒng)治工具的事實,分析了科學技術(shù)與政治統(tǒng)治之間的關(guān)系問題。
法蘭克福學派沿著盧卡奇的思想傳統(tǒng),對科學技術(shù)與政治統(tǒng)治之間的關(guān)系問題進行了全面的研究,這成了其科學技術(shù)觀的一個主題。霍克海默和阿多爾諾在《啟蒙的辯證法》一書中認為,隨著科學技術(shù)的進步,人對自然的控制能力大大加強了,但這種控制最終是以人對人的統(tǒng)治作為代價的,即科學技術(shù)既是人控制自然的工具,反過來變成人對人統(tǒng)治的手段。在他們看來,在當代社會,統(tǒng)治的原則已發(fā)生了變化,原來的那種基于野蠻力量的統(tǒng)治讓位給一種更巧妙的統(tǒng)治,即借助科學技術(shù)手段,統(tǒng)治階級的意志和命令被內(nèi)化為一種社會及個人心理,技術(shù)已經(jīng)成為新的控制形式。霍克海默和阿多爾諾提出的基本論斷是“技術(shù)的基本原理就是統(tǒng)治的基本原理”,因為人運用理性工具不斷征服自然,以技術(shù)的進步、效率的提高作為合理性活動的準則,這本身就體現(xiàn)了人對自然的統(tǒng)治欲。而從文藝復興時期開始,由于科學技術(shù)與政治統(tǒng)治的直接聯(lián)結(jié),并且隨著科學技術(shù)的發(fā)展,生產(chǎn)工具越來越復雜、精確,反過來導致對人的奴役和控制能力的增強,人日益變成機器操縱的對象,因而科學技術(shù)體現(xiàn)了人對人的統(tǒng)治欲。這種人對自然的統(tǒng)治和人對人的統(tǒng)治充分說明技術(shù)合理性又與政治統(tǒng)治結(jié)下不解之緣,技術(shù)的合理性變成了統(tǒng)治的合理性。
探索設計藝術(shù)與數(shù)字科技的結(jié)合
摘要:我們已經(jīng)不能再把藝術(shù)設計理解為一個狹隘的概念,數(shù)字技術(shù)被廣泛應用于藝術(shù)設計領域,這就意味著人們的設計觀念與設計思維已經(jīng)在一定范圍內(nèi)和一定程度上發(fā)生了新的變化。設計師必須學會掌握將知識轉(zhuǎn)化成電腦語言的工具和技巧,在科學技術(shù)與藝術(shù)設計之間尋找一個平衡的支點。設計師的藝術(shù)感受力和創(chuàng)造力依然是設計作品的靈魂,這是我們正確認識數(shù)字技術(shù)與藝術(shù)設計和諧發(fā)展非常關(guān)鍵的一點。
關(guān)鍵詞:數(shù)字技術(shù)設計藝術(shù)觀念
設計藝術(shù)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產(chǎn)生以來,經(jīng)歷了從工業(yè)化社會到信息化社會的歷程,最終走上了數(shù)字化的道路。在數(shù)字技術(shù)條件下的設計藝術(shù),所用的工具和材料在現(xiàn)實的物質(zhì)觀念中是不存在的,一切都是在處理數(shù)字所組成的虛擬概念,而非現(xiàn)實世界中的物質(zhì)實體,但創(chuàng)造出來的視覺形象卻讓人感覺是真實的。傳統(tǒng)的設計基礎被沖破,“傳統(tǒng)的設計觀念已從有形的物資領域擴展到了無法觸摸的程序領域。”數(shù)字化觀念已經(jīng)悄悄地滲入到現(xiàn)代人的意識形態(tài)。
一、數(shù)字技術(shù)在設計藝術(shù)領域的廣泛應用,使人們開始對多媒體、交互式的視覺交流方式進行深入探究。
設計藝術(shù)的形式也由以往媒體形式上的物資化、平面化、靜態(tài)化以及單一化開始逐漸向虛擬化、空間化、動態(tài)化和媒體的綜合化方向轉(zhuǎn)變。傳統(tǒng)的設計工具與媒體形式的巨大變革,極大地改進了設計的技術(shù)手段,同時改變了傳統(tǒng)的設計程序與設計方法。虛擬的數(shù)字化圖形、圖像處理技術(shù)與數(shù)字網(wǎng)絡技術(shù)甚至還改變了產(chǎn)品開發(fā)及銷售模式,從而引發(fā)了設計模式及設計生產(chǎn)劃時代的變革。
最早的設計藝術(shù)是從大美術(shù)中衍生出來的,這使傳統(tǒng)的設計主要以技法表現(xiàn)為中心,而傳統(tǒng)的設計圖紙只能用手工的方式進行表現(xiàn),也使得設計者將大量時間花費在技法上,這在當時的技術(shù)條件下是無可非議的。數(shù)字化計算機技術(shù)“以屏幕顯示的方式開辟了設計傳達的新領域”,設計的每一個過程可視化,使設計變得更為直觀;交互式的人機交流方式和用戶參與的全新人機界面,改變了設計與生產(chǎn)分離的傳統(tǒng)被動式的設計模式;互聯(lián)網(wǎng)的信息資源無限、圖文互動與全球化的交互信息,使地緣間的界限被逐步淡化和消除。數(shù)字技術(shù)融入設計藝術(shù)創(chuàng)作過程所帶來的是更為真實的表現(xiàn)、更為便捷的方法、更為迅速的交流、更為拓展的思路等,它突破了以往許多在創(chuàng)作思維、創(chuàng)作方法、創(chuàng)作表現(xiàn)方面的限制,觀念的形成、市場調(diào)查、設計戰(zhàn)略的組織等成為當代設計師面臨的主要任務。
哲學基本題
哲學發(fā)展的階段性,是由一些重要因素所決定的。這些因素主要是指在不同歷史階段中:(一)扮演主要角色的關(guān)鍵哲學家;(二)有決定性影響和有分量的哲學著作;(三)重大的理論爭論的內(nèi)容及其結(jié)果;(四)社會和文化層面的重要歷史事件的不可替代性。所有這些因素,都呈現(xiàn)非常明顯的‘一次性’或‘不可重復性’,對哲學思想的創(chuàng)造活動,提供了獨特的歷史條件和精神力量;但是,同一般歷史一樣,思想史和哲學史也經(jīng)常走回頭路,在不可預測的力量的影響下,往往出現(xiàn)多次重復、回歸、退后、迂回、旋轉(zhuǎn)和‘反芻’,使當代西方哲學思想的演變過程,既顯示歷史延續(xù)性的特征,又展現(xiàn)斷裂、重疊、偶然性和突發(fā)性的特殊軌跡。
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之后,在西方哲學思想演變過程中,就其社會基礎而言,有兩個重要的分水嶺:1968年的學生運動和八十年代末發(fā)生的五大歷史事件:(1)全球化和消費文化的洪水般泛濫、(2)蘇聯(lián)東歐國家集團的垮臺、(3)歐盟的擴大、(4)基因工程和電子數(shù)碼化的現(xiàn)代科學技術(shù)的突飛猛進、(5)恐怖活動及突發(fā)性社會和自然災害事件的頻繁發(fā)生。
如果說,1968年學生運動充分暴露了西方思想和文化的總危機的話,那么,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后發(fā)生的上述五大歷史事件,則成為當代哲學理論探討的最重要的社會文化土壤,并把1968年后所顯示的西方哲學思想的矛盾及其解決的可能性,具體地在新世紀的人類文化平臺上展現(xiàn)出來。
正是在總結(jié)1968年學生運動和80年代末的五大社會事件的歷史經(jīng)驗之后,西方哲學全面地反省西方傳統(tǒng)的根本問題,即主客體的相互關(guān)系以及由此建構(gòu)的本體論、認識論和倫理基本原則,使近半個世紀以來,由現(xiàn)代分析哲學、現(xiàn)象學、新馬克思主義、解構(gòu)主義、后結(jié)構(gòu)主義、后現(xiàn)代主義和新文化符號論所集中批判的哲學傳統(tǒng),進一步得到全面的更新,也使之從原有的‘主客二元對立’模式、人本中心主義、邏輯中心主義、語音中心主義、西方種族中心主義的約束中解脫出來,重新探索新世紀的多元文化模式的創(chuàng)造可能性。
當然,當代西方哲學的理論探討方向,也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于各個卓越的哲學家個人的思想創(chuàng)造能力、個人的理論旨趣及其思想風格。在這方面,思想家的個性、才華及其獨特性,含有很大的偶然性、神秘性和誘惑力,是無法從社會文化基礎的總體角度來分析的。
在當代西方哲學理論探討中,做出重要貢獻的思想家,除了原來屬于上一代、并在當前哲學創(chuàng)造中繼續(xù)發(fā)生重要影響的利科(PaulRicoeur,1913-2005)、漢斯·約納斯(1903-1993)、福柯、德里達、克勞特·勒福特(ClaudeLefort,1924-)、約翰·羅爾斯(JohnRawls,1921-2002)、海拉里·普特南(HilaryPutnam,1926-)、艾耶爾(AlfredJulesAyer,1910-1989)、尼克拉斯·魯曼(NiklasLuhmann,1927-1998)、迦達默(Hans-GeorgGadamer,1900-2002)、保爾·洛朗琛(PaulLorenzen,1915-1994)、卡姆拉(WilhelmKamlah,1905-1976)、伊爾丁(Karl-HeinzIlting,1925-1984)、庫諾·洛朗茲(KunoLorenz,1932-1994)、布魯門貝爾格(HansBlumenberg,1920-1996)、莊·弗朗斯瓦·利歐塔(Jean-Fran?oisLyotard,1924-1998)、姚斯(HansRobertJau?,191-1997)、哈伯馬斯、布迪厄(PierreBourdieu,1930-2002)、米歇·昂利(MichelHenry,1922-2002)以外,新冒現(xiàn)出來的思想明星,在法國,有莊·呂克·馬里墉(Jean-LucMarion,1946-)、賈克·達敏尼奧(JacquesTaminiaux)、艾麗安·埃斯古巴(ElianeEscoubas)、馬克·里希爾(MarcRichir)、莊·弗朗斯瓦·古爾丁(Jean-Fran?oisCourtine)、約斯琳·貝努瓦(JocelynBenoist)、斐利普·索耶(PhilippeSollers,1936-)、阿蘭·巴迪烏(AlainBadiou,1937-)、莊·呂克·南西(Jean-LucNancy,1940-)、柯里斯蒂娃(JuliaKristeva,1941-)、貝爾納特·亨利·列維(Bernard-HenriLévy,1948-)、阿蘭·雷諾(AlainRenaut)、德尼·康布斯納(DenisKambouchner)及弗朗斯瓦·拉呂爾(Fran?oisLaruelle)等;在德國,有彼得·斯洛德岱克(PeterSloterdijk,1947-)、米凱爾·特尼森(MichaelTheunissen,1932-)、赫爾斯特(DetlefHorster)、馬爾登(EkkehardMartens)、曼弗列德·李德爾(ManfredRiedel,1936-)、弗里特里希·卡姆巴爾德(FriedrichKambartel,1935-)、施威默爾(OswaldSchwemmer,1941-)、彼得·雅尼斯(PeterYanich,1942-)、居爾根·密特爾斯特拉斯(JürgenMittelstrass,1936-)、阿瑟爾·荷內(nèi)克(AxelHonneth)、奧德弗里德·赫弗(OtfriedH?ffe,1943-)、喬治·墨格爾(GeorgMeggle,1944-)、漢斯·約阿斯(HansJoas,1948-)、克羅爾斯·奧弗(KlausOffe,1940-)、阿爾布列斯·維爾默(AlbrechtWellmer,1933-)、巴基斯(GüntherPatzig,1926-)、圖根哈特(ErnastTugendhat,1930-)、羅伯特·斯貝曼(RobertSpaemann,1927-)、赫爾曼·呂伯(HermannLübbe,1926-)、奧多·馬瓜德(OdoMarquard,1928-)及克勞斯·貢德爾(KlaussGünther)等人,而在英、美、加等英語國家,有阿拉斯代爾·麥凱因戴爾(AlasdairMacIntyre,1929-)、約納丹·伯內(nèi)特(JonathanBennett,1930-)、克里普克(SaulA.Kripke,1940-)、羅迪(RichardRorty,1931-)、諾奇克(RobertNozick,1938-)、托馬斯·納吉爾(ThomasNagel,1937-)、理查德·蒙達戈(RichardMontague,1930-)、尼克拉斯·雷舍(NicholasRescher,1928-)、約翰·席爾勒(JohnR.Searle,1932-)、卓姆斯基(NoamChomsky,1928-)、托馬斯·麥卡錫(ThomasMcCarthy)、戴維斯·路易斯(DavidLewis,1941-)、泰勒(CharlesTylor,1931-)及達尼爾·德內(nèi)特(DanielDennett,1942-)等;意大利則有吉亞尼·瓦迪摩(GianniVattimo,1936-)、艾柯(EmbertoEco,1932-)及埃馬努爾·舍韋里諾(EmmanuelSeverino,1929-)等。
和鄧小平科技思想對比
【關(guān)鍵詞】/鄧小平/科學技術(shù)/理論/比較
MaoTse-Tung/DengXiao-ping/scienceandtechnology/theoretical/comparison
【正文】
中圖分類號:NO
、鄧小平作為中國共產(chǎn)黨第一代、第二代領導集體的核心,在領導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都形成了自己的科技思想。但是,由于歷史條件和認識程度的不同,他們所闡發(fā)的理論側(cè)重點又有所差別。因此,分析和比較、鄧小平的科技思想,對于我們今天更好地學習和領會思想、鄧小平理論,深入理解和全面實施“科教興國”戰(zhàn)略,具有重要的現(xiàn)實意義。
一、關(guān)于科技發(fā)展地位:從的“向科學進軍”到鄧小平的“科學技術(shù)是第一生產(chǎn)力”
醫(yī)學人文科學思考
1醫(yī)學的人文科學性質(zhì)的界定
醫(yī)學的人文科學性質(zhì)是相對醫(yī)學的自然科學性質(zhì)而言的。醫(yī)學的自然科學性質(zhì)十分顯著。首先,作為醫(yī)學研究對象的人,具有自然屬性。其次,醫(yī)學研究和醫(yī)療活動具有豐富的自然科學內(nèi)涵。醫(yī)學作為一門應用學科對自然科學基礎學科、技術(shù)學科的依賴非常明顯。醫(yī)學在具有顯著的自然科學性質(zhì)的同時,還具有顯著的人文科學性質(zhì)。首先,作為醫(yī)學研究對象的人,具有人文屬性。人不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社會存在物,人之為人,就在于其有精神活動、能夠能動地改造環(huán)境;人以社會的方式存在,人的生存不僅要與外界交換物質(zhì),而且要與他人、與社會發(fā)生這樣那樣的聯(lián)系;人的健康狀況與疾病同人的精神活動、與人賴以生存的社會環(huán)境有著直接或間接的聯(lián)系;醫(yī)學對健康和疾病的認識也必須建立在對人的精神活動的認識、對人與社會的聯(lián)系的基礎之上。其次,人文科學也是認識人的健康和疾病的重要工具。醫(yī)學作為一門應用學科依賴于人文科學,包括哲學、心理學、社會學在內(nèi)的許多學科也是醫(yī)學發(fā)展的基礎。這些學科已經(jīng)或正在為醫(yī)療衛(wèi)生活動、醫(yī)學研究、醫(yī)學人才培養(yǎng)提供方法和途徑,成為醫(yī)學發(fā)展的重要基礎。醫(yī)學的人文科學性質(zhì)還突出地表現(xiàn)為,醫(yī)學研究和醫(yī)療活動是以對人的尊重、對人的生命的關(guān)愛為基礎的,沒有對人的尊重和關(guān)愛就沒有醫(yī)學,治病救人,提高人的健康水平永遠是醫(yī)學的永恒目標,是醫(yī)務工作者不懈的追求。醫(yī)學的人文科學性質(zhì)與醫(yī)學的自然科學性質(zhì)共存于醫(yī)學活動之中,二者既相互區(qū)別又緊密聯(lián)系,相互交融,猶如一枚硬幣的兩面,不可分割。人的健康和疾病是自然因素、心理、社會因素共同作用的結(jié)果;人們在與疾病的斗爭中逐步認識到健康和疾病的自然性質(zhì)和人文性質(zhì),并積累了含自然科學技術(shù)和人文科學方法在內(nèi)的諸多預防、診治疾病的方法。
2新醫(yī)學模式的確立與醫(yī)學人文科學性質(zhì)的重新發(fā)現(xiàn)
綜觀醫(yī)學發(fā)展的歷史,對醫(yī)學的人文科學性質(zhì)的主動自覺認識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在相當長的時期里,醫(yī)學的人文科學性質(zhì)并未得到應有的重視,甚至被忽略了。時至今日,仍存在模糊認識,仍有人僅僅看到醫(yī)學的自然科學性質(zhì),將醫(yī)學限定為自然科學。原因何在?這主要根源于醫(yī)學的內(nèi)部,是醫(yī)學自身發(fā)展的結(jié)果,確切地說,與醫(yī)學在近代以后的發(fā)展直接相關(guān)。在古代,無論是東方還是西方,在醫(yī)家認識和預防、診治疾病的具有籠統(tǒng)模糊猜測特征的整體觀念中是包含著“自然科學”、“人文科學”(這里的“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帶引號是因為當時的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還不是16世紀以后的嚴格意義上的科學)的觀念和方法的。西方醫(yī)圣希波克拉底強調(diào)“醫(yī)術(shù)是一切技術(shù)中最美和最高尚的”,醫(yī)生應具有“利他主義、熱心、謙虛”的品質(zhì),人的疾病與人的生活方式相關(guān);中國唐代藥王孫思邈強調(diào)“大醫(yī)精誠”,都是很好的證明。盡管古代醫(yī)家的人文觀念、他們借助當時的人文知識認識健康和疾病現(xiàn)象與醫(yī)學的原始形態(tài)(尚不獨立)相關(guān)聯(lián),在本質(zhì)上,是一種被動和無奈,但融自然科學萌芽和人文科學萌芽于一體的古代醫(yī)學注重整體的觀念無疑是正確的。
近代以后,情況發(fā)生了變化。近代科學技術(shù)的發(fā)展武裝了醫(yī)學,為醫(yī)學的發(fā)展開辟了道路,使醫(yī)學日益成為沿著生物學、化學、物理學等自然科學思路和方法認識并解決問題的學科,使醫(yī)學形成了生物醫(yī)學的觀念和模式。與古代醫(yī)學比較,精確、清晰成為近代醫(yī)學的特征。但這只是事情的一個方面。近代醫(yī)學在注重精確、清晰的同時,不經(jīng)意地忽略了古代醫(yī)學的整體觀念。其中,包括對社會、心理因素致病作用和預防、診治疾病的人文科學方法的忽略。用歷史的眼光看,這是一種必然,是近代醫(yī)學發(fā)展的代價。因為,當時醫(yī)學的獨立和以科學技術(shù)為基礎的發(fā)展,激發(fā)了醫(yī)生們的興趣和熱情,占用了他們的精力和時間,也限制了他們的視野,使他們看不到醫(yī)學的人文科學性質(zhì),忽略、甚至遠離了人文科學。當然,醫(yī)學的人文科學性質(zhì)被忽略也有醫(yī)學之外的原因,與人文科學的發(fā)展水平低下有關(guān)。提出并重視醫(yī)學人文科學研究是以當代人文科學研究為背景的。應當說,當前的人文科學研究為醫(yī)學人文科學研究創(chuàng)造了前所未有的條件。隨著醫(yī)學的發(fā)展,醫(yī)學的人文科學性質(zhì)終于得到應有的關(guān)注。筆者認為,醫(yī)學的人文科學性質(zhì)的凸顯與醫(yī)學模式的轉(zhuǎn)換直接相關(guān)。生物-心理-社會醫(yī)學模式對生物醫(yī)學模式的取代,使人們重新發(fā)現(xiàn)了醫(yī)學的人文科學性質(zhì)。醫(yī)學模式轉(zhuǎn)變是在根本的意義上即在關(guān)于醫(yī)學本質(zhì)的意義上對醫(yī)學的基本理念、基本原則、基本結(jié)構(gòu)的反思,對醫(yī)療衛(wèi)生服務的目的、原則、方式的反思。
這一反思既是對現(xiàn)代醫(yī)學進步和醫(yī)療衛(wèi)生服務的理論層面的總結(jié),更是對醫(yī)療衛(wèi)生服務中存在的過分強調(diào)醫(yī)學的自然科學性質(zhì)、技術(shù)性質(zhì),忽略甚至無視醫(yī)學的人文科學性質(zhì)傾向的糾正。醫(yī)學模式不僅植根于醫(yī)學活動,而且反作用于醫(yī)學活動。在近代醫(yī)學基礎上建立的,促進了近、現(xiàn)代醫(yī)學的發(fā)展生物醫(yī)學模式,由于其顯著的片面性最終成為制約醫(yī)學發(fā)展的桎梏。而以20世紀中葉以來自然科學進步、人文科學進步特別是醫(yī)學自身發(fā)展為基礎的生物-心理-社會醫(yī)學模式,則為醫(yī)學的發(fā)展開辟了廣闊的天地。醫(yī)學進入了人文科學的視野,人們重新看到了醫(yī)學的人文性質(zhì)。新醫(yī)學模式的建立揭示了醫(yī)學的人文科學性質(zhì),成為落實醫(yī)學的人文科學性質(zhì)的推動力量。但是,正如新醫(yī)學模式的落實不盡如人意一樣,醫(yī)學的人文科學性質(zhì)也未得到應有的重視。因為,新醫(yī)學模式的確立和在實踐中的實施是一個過程,醫(yī)學的人文科學性質(zhì)被普遍認同也是一個過程。令人欣慰的是,新醫(yī)學模式在實踐中的實施已經(jīng)得到了越來越廣泛的認同,成為醫(yī)學研究和臨床工作的重要理念和指導思想;醫(yī)學的人文科學性質(zhì)也在不斷深入人心,成為人們的共識。
相關(guān)欄目更多
當代文學 當代文學論文 當代文學作品 當代建筑論文 當代經(jīng)濟管理 當代城市設計 當代美術(shù)論文 當代金融論文 當代經(jīng)濟發(fā)展 當代語文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