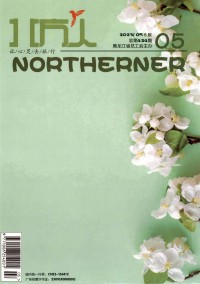楊絳百歲感言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嗎?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5篇楊絳百歲感言范文,相信會(huì)為您的寫作帶來幫助,發(fā)現(xiàn)更多的寫作思路和靈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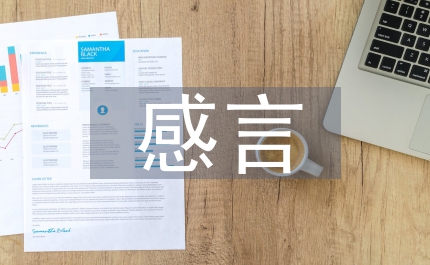
楊絳百歲感言范文第1篇
我愛大自然,其次就是藝術(shù);
我雙手烤著生命之火取暖;
火萎了,我也準(zhǔn)備走了。
這是英國(guó)詩人沃爾特?蘭德晚年寫下的詩句,題目是《生與死》。楊絳喜歡這個(gè)關(guān)于火焰的譬喻,把它譯成中文,置于晚年散文集《楊絳散文》的卷首題詞。
105歲,不可謂不長(zhǎng)壽。但火萎了,她利利落落起身,便也走了。
作為一個(gè)文化世紀(jì)老人,楊絳的身體狀態(tài)一直牽著很多人的心。這段時(shí)間,先是“病危”的傳言讓許多顆心被提到嗓子眼,又是各方辟謠讓它們放回肚子里。正當(dāng)人們以為不過是一場(chǎng)尋常小恙時(shí),猝不及防地,卻等來了最終被官方證實(shí)的消息:作家、翻譯家、中國(guó)社會(huì)科學(xué)院榮譽(yù)學(xué)部委員、外國(guó)文學(xué)研究所研究員楊季康(筆名:楊絳)先生,以105歲高齡于2016年5月25日1時(shí)10分在京逝世。
楊絳有遺愿,希望去世不作為新聞,火化后再發(fā)訃告。但在這樣一個(gè)新媒體、自媒體迭出的時(shí)代里,可以想來,這個(gè)遺愿實(shí)現(xiàn)起來太難。一時(shí)間,緬懷和悼詞呼嘯而來,無處不是“最賢的妻,最才的女”,乃至假托她“百歲感言”的“世界是自己的,與他人毫無關(guān)系”。這種山呼海嘯,大概不是楊絳自己愿意看到的吧――2012年,社科院院長(zhǎng)陳奎元看望她時(shí),她曾提出了三個(gè)要求:一、去世后,不開追悼會(huì);二、不受奠儀;三、至多七八至親送送。
作為一個(gè)有影響的文化人,她低調(diào)得有些不可思議,像個(gè)古代的隱士。這些年來,她閉門謝客,拒絕采訪,甚至不參加自己文集的會(huì)。九十大壽,一百大壽,這些對(duì)旁人來說格外重要的節(jié)點(diǎn),她也都謝絕了上門祝壽。她愛用“隱身衣”的比喻,許多年里,她都披著一件“隱身衣”,“保其天真,成其自然,潛心一志完成自己能做的事”。
因了這“潛心一志”,四十年代,她有成名劇本《弄真成假》《稱心如意》,被稱為“喜劇雙璧”,被和李健吾垂青;上世紀(jì)八九十年代,她有長(zhǎng)篇小說《洗澡》、散文《干校六記》等,成了一個(gè)重要的現(xiàn)代知識(shí)分子創(chuàng)作現(xiàn)象;新世o以來,93歲時(shí)寫了她和錢鐘書、女兒阿瑗的《我們仨》,96歲時(shí)出了《走在人生邊上――自問自答》,103歲時(shí)出了《洗澡》的續(xù)集《洗澡之后》。還有翻譯,包括最為重要的《堂吉訶德》;還有為丈夫編的作品,包括由商務(wù)印書館推出的72卷本的錢鐘書手稿集。很難想象,若不是披著“隱身衣”,這瑣碎雜亂的工作,如何能夠延續(xù)許多年,并安安心心地完成。
“我無法確知自己還能往前走多遠(yuǎn),壽命是不由自主的,但我很清楚我快‘回家’了。我得洗凈這一百年沾染的污穢回家。我沒有‘登泰山而小天下’之感,只在自己的小天地里過平靜的生活。”這是她在2011年100歲誕辰時(shí),于《文匯報(bào)?筆會(huì)》上所做的一次筆談專訪。她早已做好火焰枯萎的準(zhǔn)備。“邊上”,是她對(duì)于年歲的自我意識(shí),是她以一種并不清晰唯一的模樣游走于文學(xué)史上的姿態(tài),也是她為人生劃定的位置。
(選自《北京晚報(bào)》2016年5月27日,有刪節(jié))
■
楊絳先生走了,人間再無“我們仨”。
楊絳百歲感言范文第2篇
節(jié)操不能帶來財(cái)富、名利,但是可以讓人聆聽到自然的寧靜。李毅元的耳朵聽不到那些細(xì)微的聲音,但是這份寧靜,他安享了。
沉浸在藝術(shù)中才讓他快活
這位77歲的老畫家,平日獨(dú)居,這兩天桂林陰雨蒙蒙,膝蓋更疼起來,上樓多少有些蹣跚。進(jìn)入家門,你幾乎分不清這是畫室還是住處,因?yàn)閺拈T口到客廳,再到各個(gè)房間,都掛滿了他的作品。大大小小的寫生油畫,有人物、靜物、風(fēng)景。獎(jiǎng)狀和各類邀請(qǐng)函,被他藏在書房的抽屜里。
前一陣,他的眼睛因白內(nèi)障動(dòng)過手術(shù),恢復(fù)后,他只覺自己好像回到年輕時(shí)期。他現(xiàn)在仍然依靠靈感和熱情來創(chuàng)作。沒靈感時(shí),一月半月都不動(dòng)筆,只是彈彈琴,看看書。一旦靈感來了,半夜都要從被窩里爬起來,想睡也睡不著,靈感的延續(xù)一般是一個(gè)小時(shí)左右,剩下就靠一個(gè)人的毅力了。李毅元說,多年來的畫畫磨練了他的意志。
畫畫時(shí),整個(gè)人全神貫注,這是他學(xué)畫時(shí)就養(yǎng)成的習(xí)慣,別的同學(xué)聊天、走動(dòng),他自己靜靜地畫畫。畫到激動(dòng)的地方,他拿畫筆用力去打畫板,他引用李可染的話形容自己創(chuàng)作時(shí)的狀態(tài):無鞍騎野馬,赤手抓毒蛇,老虎搏大象,猶如在搶林彈雨之中的高度集中。李毅元對(duì)此深有體會(huì),“這是一種本能”。
他的鋼琴上放著翻開的兩本琴譜,是庫勞的《小奏鳴曲》和俄羅斯民歌《伏爾加船夫曲》。李毅元現(xiàn)在每天欣賞音樂,為貝多芬的《命運(yùn)交響曲》震撼,也在賀綠汀田園牧歌般的旋律中如癡如醉。也常常自己彈奏,陶醉其中。他從初中學(xué)習(xí)鋼琴和小提琴,音樂伴隨了他一生。“音樂美感的熏陶和感化也難免在繪畫創(chuàng)作中自然流露,這種流露如同作畫一樣,最要天真自然,發(fā)于無意者為上。”李毅元的博客里唯一的一首曲子,是西班牙小提琴家薩拉薩蒂的《流浪者之歌》,他說大學(xué)時(shí)第一次聽到這首曲子,就覺得它奏出了自己的心聲。跌宕激昂的旋律,講述流浪的吉普賽人被驅(qū)逐、孤獨(dú)的心境,卻熱情勇敢地面對(duì)生活的態(tài)度。
那個(gè)年代,人們持守著節(jié)操
上個(gè)世紀(jì)五六十年代,李毅元在中南美專、廣州美院學(xué)習(xí)。當(dāng)時(shí)美院聚集了一大批優(yōu)秀的教師,如郭紹綱、王道源、惲圻蒼、張彤云、徐堅(jiān)白等。李毅元懷念五十年代美院的學(xué)風(fēng),“榮譽(yù)感、正義感占主導(dǎo)”,也懷念他的恩師們。在班上,李毅元是班長(zhǎng),也是郭紹綱最看重、信賴的學(xué)生,郭紹綱留學(xué)蘇聯(lián),比李毅元大不了幾歲,兩人一生結(jié)下了深厚的師生友誼。
時(shí),團(tuán)支書想讓他揭發(fā)自己的老師,他硬是一句話都沒說。七十年代他在湖南任教時(shí),遭遇和老師相似的處境,他的學(xué)生也這樣維護(hù)老師,與他巧合般地相似,令他至今欣慰。
他在湖南任教十余年,參與湖南師范藝術(shù)系前身――湖南藝術(shù)學(xué)院的籌建工作。他和學(xué)生年齡相近,教學(xué)認(rèn)真,那時(shí)學(xué)生經(jīng)常聚在一起畫畫,然后叫上李老師點(diǎn)評(píng)教導(dǎo),或是在家里,或是在外面寫生。那是后的77級(jí),所以學(xué)生格外地發(fā)狠。李毅元的女兒雅日,正是在這批學(xué)生中間長(zhǎng)大的,李毅元教學(xué)時(shí)總帶著女兒,她為父親定畫框,看著父親畫畫,和父親學(xué)拉小提琴。李雅日至今記得,父親經(jīng)常在晚上十點(diǎn)多牽著她的小手回家。就讀國(guó)畫系、上過他人體結(jié)構(gòu)課的譚仲池,現(xiàn)在是湖南省美協(xié)主席,油畫系的蕭沛蒼是湖南美術(shù)出版社前社長(zhǎng),下個(gè)月滿頭銀發(fā)的蕭老還要來老師這里一同畫畫交流,住上幾日。
李毅元回憶他寫信給身在美國(guó)的老師徐堅(jiān)白,感謝老師的教導(dǎo)。老師回信說,沒有哪個(gè)老師不愛惜學(xué)生,我是愛惜你的才華……李毅元回憶到這里,哽咽難言。
李毅元的手機(jī)里,存著學(xué)生發(fā)給他的《楊絳百歲感言》,一句句指給我看:“我沒有‘登泰山而小天下’之感,只在自己的小天地里過平靜的生活。細(xì)想至此,我心靜如水,我該平和地迎接每一天,準(zhǔn)備回家。”李毅元深佩錢鐘書、楊絳夫婦二人,無論在何種歲月,只專注讀書。
李毅元最崇尚的兩位藝術(shù)家,一是李鐵夫,一是黃賓虹。李鐵夫是中國(guó)油畫的先驅(qū)者,也是民主革命家,國(guó)學(xué)和油畫造詣都很好,只因在歐洲留學(xué)了四十多年,不為國(guó)人所知。黃賓虹是中國(guó)畫的山水畫家,他的一生從來沒有光輝過,一直處在邊緣,直到過世后才慢慢被發(fā)現(xiàn)和認(rèn)可。李毅元稱他們是“真正的、百分之百、純粹的”藝術(shù)家。李毅元稱自己也一直處在邊緣,他臨摹兩位畫家的作品,也從他們的人品和經(jīng)歷中聊以。
真實(shí)的才可以永恒
1985年,李毅元回到自己闊別三十年的家鄉(xiāng),開始籌建廣西師范大學(xué)藝術(shù)系。他拒絕了恩師郭紹綱去廣州美院教書的邀請(qǐng),留在年邁的老母親身邊,也滿懷壯志想要建起理想的藝術(shù)系。因此他主張向全國(guó)招賢納士,選擇優(yōu)秀的教師來,拒絕了桂林本地藝術(shù)圈的人,因此遭到嫉恨,許多人后來通過關(guān)系也進(jìn)入了師大,他因此遭到排擠。
桂林旅游開發(fā)很早,上世紀(jì)八十年代,以旅游帶動(dòng)的商業(yè)氣息已很濃厚,藝術(shù)也受到波及。李毅元無力改變這樣的風(fēng)氣,他能做的,只是堅(jiān)持自己的創(chuàng)作,不去迎合,也不往來。桂林在藝術(shù)方面信息閉塞,視野狹窄,李毅元形容自己像一只離群的孤雁,缺少可以交流和分享的同道。他的朋友、留日畫家李駱公當(dāng)時(shí)斷言,李毅元在這里十年就完了。李毅元笑著說,他昨天晚上還在畫畫。
“我一向不趕時(shí)髦,我談的都是一些永恒性的東西。我覺得一個(gè)人沒有正義感是不行的,我崇尚真善美,但是在這個(gè)時(shí)代不一定行得通,現(xiàn)在假的太多了,假職稱、假產(chǎn)品、假畫,講話也是假的,我都很討厭這些。我比較喜歡實(shí)實(shí)在在的。”從事寫實(shí)油畫創(chuàng)作幾十年,他認(rèn)為真實(shí)中,有美,有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