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宣告死亡的構成要件
前言:本站為你精心整理了論宣告死亡的構成要件范文,希望能為你的創(chuàng)作提供參考價值,我們的客服老師可以幫助你提供個性化的參考范文,歡迎咨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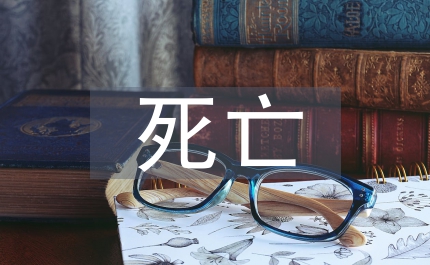
摘要:我國民法典應沿用宣告死亡的概念和制度。因危難事件下落不明的期間與一般意外事故下落不明的期間應分別規(guī)定。在戰(zhàn)爭期間下落不明宣告死亡,軍人和平民要區(qū)別對待。死亡宣告申請權不應有順序之分,可賦予檢察機關申請和撤銷死亡宣告權。原則上被宣告死亡人的死亡時間為法定下落不明期間屆滿之日。宣告死亡判決確定的死亡日期與真實死亡日期不一致為撤銷死亡宣告事由,宣告死亡的效力及于被宣告死亡人失蹤前以住所為中心的民事法律關系。
關鍵詞:宣告死亡構成要件
一、實質(zhì)要件:自然人下落不明達到法定期間
(一)下落不明期間根據(jù)引起下落不明的原因不同分為普通期間和特殊期間
1.普通期間。我國法律規(guī)定一般情況下落不明滿4年,利害關系人可申請宣告其死亡。德國法律將普通期間規(guī)定為10年,《法國民法典》規(guī)定普通期間為推定失蹤判決作出后經(jīng)過10年,《意大利民法典》規(guī)定為10年,俄羅斯聯(lián)邦民法典規(guī)定為5年,日本法律和我國臺灣地區(qū)均規(guī)定為7年。[1]相比之下我國的期間規(guī)定較短,亦有學者認為應借鑒國外的立法對期間加以延長。筆者認為,現(xiàn)今社會人們活動領域擴大,通信手段日新月異,信息的溝通交流日益迅捷;況且社會經(jīng)濟流轉(zhuǎn)速度加快,以個體為中心的權利義務變動頻率亦日趨加速,所以規(guī)定較長期間已不符合現(xiàn)實生活的需要,不僅起不到保護利害關系人的利益,只能使以自然人為中心的法律關系長期僵化。我國的期間長短規(guī)定較為合理,無變動必要。
宣告死亡的下落不明期間是否因失蹤人的年齡而各國和地區(qū)區(qū)別對待?德國法律規(guī)定已滿80歲者下落不明5年即可宣告死亡而不拘泥于10年界限。我國臺灣地區(qū)法律規(guī)定,一般原因失蹤下落不明期間為7年,而80歲以上年邁者失蹤則為3年。此種區(qū)別對待看似符合客觀規(guī)律,人終有生命極限,而年長者相對接近,在同樣失蹤情況下年長者較年輕者生存希望更為渺茫,在長期下落不明的情況下,為年長者規(guī)定較短的期間,有利于及時結(jié)束權利義務關系的不穩(wěn)定狀態(tài)。然而宣告死亡制度并非是事實判斷,而是法律擬制。在保護利害關系人的同時,也要考慮失蹤人的利益,期間長短則關系失蹤人的利益保護,賦予年長者較短期間,年輕者較長期間,將兩者置于不平等地位,似乎后者應著重保護,前者次要保護。申言之,如果以失蹤人的自然狀態(tài)不同來區(qū)分期間長短,那么患有嚴重疾病、視覺、聽覺存在嚴重障礙的失蹤人是否也規(guī)定較短的期間呢?筆者認為,我國法律不因失蹤人的自然狀態(tài)不同而區(qū)別對待,而是同等保護較為合理,值得推崇。
2.特殊期間。因意外事故下落不明,失蹤人死亡的可能性與一般情況下失蹤相比較大,故法律規(guī)定相對較短的特殊期間。我國法律規(guī)定意外事故下落不明的期間為2年,德國、日本法律規(guī)定為1年,意大利民法典規(guī)定為2年,俄羅斯民法典規(guī)定為6個月。然而意外事故當中的一些危難事件,如海難、空難、礦井瓦斯爆炸、雪崩等情況,在此類意外事故中失蹤,失蹤人生還的機會極其微小,經(jīng)過長時間有組織搜救未果的情況下,是否有必要拘泥于意外事故的期間呢?德國法律采取單獨列舉的方式,規(guī)定空難為3個月,海難為6個月。意大利和日本則沒有區(qū)分,我國《民事訴訟法》第167條規(guī)定:“因意外事故下落不明的,經(jīng)有關機關證明該自然人不可能生存,利害關系人申請宣告死亡的,不受民法有關宣告死亡之特別期間的限制。”此規(guī)定被梁慧星教授主持的中國民法典立法研究課題組編訂的《民法典總則草案建議稿附理由》(以下簡稱《建議稿》)借鑒,《建議稿》第43條規(guī)定“自然人下落不明的時間,從其最后離開住所或者居所而下落不明的次日開始計算。戰(zhàn)爭期間下落不明的,從戰(zhàn)爭結(jié)束之日開始計算。因意外事故下落不明的,從事故發(fā)生之日開始計算”。第44條規(guī)定;“自然人在危險事故中下落不明時,經(jīng)有關機關根據(jù)現(xiàn)實情況確認其絕無生存可能,利害關系人申請宣告死亡不受本法42條第1款第(二)項規(guī)定期間的限制。”[2]此類規(guī)定有利于迅速結(jié)束權利義務的不確定狀態(tài),有疑問的是“絕無生存可能”是否還屬于宣告死亡的范疇。宣告死亡制度是出于保護利害關系人的目的,運用高度蓋然性原理,將持續(xù)一定期間的生死不明狀態(tài)通過法定程序予以確定,實為法律擬制,而非事實上確定,以滿足現(xiàn)時需要。而“絕無生存可能”已經(jīng)不是蓋然性而是確定性的表述,另賦予“有關機關根據(jù)現(xiàn)實情況確認”“絕無生存可能”的事實,會制約宣告死亡制度功能的發(fā)揮。例如確認的作出要受各種主客觀因素的影響,“有關機關”在不同危難事件中又表現(xiàn)為不同的機構,如何認定機構的公信力、權威性等都是不確定的因素,另外實際事故的調(diào)查、搜救,責任的認定時間亦不會短,未必能起到及時了結(jié)權利義務關系的效果。反而,時間的經(jīng)過具有客觀性、確定性,不會受失蹤事實以外因素的影響和制約,筆者認為在上述危險事件中下落不明,雖然失蹤人生存可能性微乎其微,但也只是高度蓋然性,而非確定性,盡量減少不確定因素對于宣告死亡制度運做的干擾,在制度設計上可以仿效德國的作法縮短危險事件的下落不明期間,從而實現(xiàn)失蹤人和利害關系人的利益平衡。
(二)下落不明期間起算點的確定
期間長短固定、期間計算起點的確定則至關重要,直接影響宣告死亡制度功能的實現(xiàn)。普通期間的計算各國通常規(guī)定為知道失蹤人最后信息之日計算。如《意大利民法典》規(guī)定自獲得最后消息之日起經(jīng)過10年,《法國民法典》規(guī)定某人停止在其住所或居所出現(xiàn),且他人無其音信,被法院判決確認推定失蹤,自推定失蹤的判決做出10年或雖無法院判決確認失蹤,但當事人停止在其住所地或居所地出現(xiàn),無信息20年以上者。德國法律規(guī)定從有最后信息起算[3]。我國《民法通則》無起算點的規(guī)定,《意見》第28條規(guī)定:“一般情況下落不明,從公民音信消失之次日起算。”探悉立法者本意,似從最后音信的次日起算,然表述上不清晰,何為“公民音信消失之次日”?況且下落不明期間失蹤人一直處于音信消失狀態(tài),究竟從哪一天起算呢?《建議稿》第43條規(guī)定“自然人下落不明的時間,從其最后離開住所或者居所而下落不明的次日開始計算”。該條規(guī)定的目的在于解決期間計算起點問題,而“下落不明的時間從下落不明的次日起算”表述不清楚,下落不明是事實狀態(tài)而不是確定的日期,與民法通則的規(guī)定犯了相同的表述錯誤,實踐中無法掌握。另下落不明關鍵是被宣告人音信的有無,下落是否確定,而與是否“最后離開住所或者居所”無關,實踐中甚至可能會出現(xiàn)被宣告人未離開住所地而符合宣告失蹤條件的,因此時間的起算點不應與住所或者居所相聯(lián)系。綜上,筆者認為應直接規(guī)定自然人下落不明的期間從最后音信的次日起算,這樣清晰、明確,易于操作。
戰(zhàn)爭期間下落不明的計算。我國法律規(guī)定戰(zhàn)爭期間下落不明的從戰(zhàn)爭結(jié)束之日起算,“然在戰(zhàn)爭失蹤,如戰(zhàn)爭延長,則于戰(zhàn)爭繼續(xù)中不得為死亡宣告,事實頗為不便。”[4]和平與發(fā)展是當今世界主題,但戰(zhàn)爭、地區(qū)沖突有時在所難免,戰(zhàn)爭的長短通常難以確定(例阿富汗戰(zhàn)爭持續(xù)20余年,伊拉克戰(zhàn)爭已經(jīng)5年),若自然人在戰(zhàn)爭中某一刻下落不明,直到戰(zhàn)爭結(jié)束時才能計算,則權利義務的不確定狀態(tài)在失蹤人最后消息到戰(zhàn)爭結(jié)束和戰(zhàn)爭結(jié)束后4年內(nèi)長期持續(xù),甚至可能由于戰(zhàn)爭的長期進行,而宣告死亡制度無法啟動,對失蹤人的利害關系人利益保護不利。《意大利民法典》規(guī)定參加戰(zhàn)爭的軍人、輔助人員和在部隊中服役而在戰(zhàn)爭期間失蹤的人員,自和平條約生效之日起經(jīng)過2年,未締結(jié)和平條約的情況下,自停止敵對狀態(tài)之日起經(jīng)過3年可以宣告死亡。《俄羅斯聯(lián)邦民法典》也對于軍人給予類似特殊規(guī)定。筆者認為這樣的規(guī)定有借鑒意義,為鼓勵軍人參加保衛(wèi)祖國戰(zhàn)爭,穩(wěn)定軍心,在宣告死亡制度下落不明期間起算點的設計上對參戰(zhàn)的軍人應給以特殊保護。因此參戰(zhàn)軍人在戰(zhàn)爭期間下落不明的,期間的起算點應為戰(zhàn)爭結(jié)束日。除此以外的自然人在戰(zhàn)爭期間下落不明的,期間的起算點以最后音信的次日為妥。
二、形式要件
(一)利害關系人申請
1.列舉加概括的方式。如《意大利民法典》規(guī)定受遺贈人、受贈人以及所有由于失蹤人的死亡能夠取得某種權利的人,遺囑繼承人、法定繼承人或他們各自的繼承人可以申請宣告死亡。我國《民法通則》無利害關系人范圍的規(guī)定,《意見》第24條規(guī)定利害關系人的范圍和順序:(1)配偶(2)父母、子女(3)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孫子女、外孫子女(4)其他有民事權利義務關系的人。
2.概括式。《法國民法典》規(guī)定任何有利害關系人和檢察院可請求法院宣告失蹤。《日本民法典》規(guī)定利害關系人可以請求失蹤宣告。
利害關系人的申請權行使是否有順序限制,《建議稿》第45條規(guī)定:“宣告死亡應由利害關系人向人民法院申請。申請宣告死亡的利害關系人,包括被申請宣告人的具有完全民事行為能力的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孫子女、外孫子女以及其他與其有民事權利義務關系的人。申請宣告死亡不受前款所列人員的順序的限制”。有疑問的是,利害關系人前加上“有完全民事行為能力的”限定詞,從反面推之,無民事行為能力和限制民事行為能力的上述人員則無申請宣告死亡的權利,只能任由權利義務處于長期不確定狀態(tài),立法理由中未見詳細說明。不具有完全行為能力的利害關系人完全可以通過人進行申請,行為人是否具有相應的民事行為能力僅影響民事行為的效力,而不表示對不同民事行為能力的人的權利進行區(qū)別對待,此項限定應取消為妥。
檢察機關能否申請宣告死亡?檢察機關作為國家司法機關申請宣告下落不明的自然人死亡是國家公權力對私法領域的介入,對其如何處理,各國立法規(guī)定不一。有些國家、地區(qū)法律確立檢察機關申請宣告死亡的權利,如意大利、法國、我國臺灣地區(qū)。筆者認為,檢察機關為宣告死亡的申請人依職權干涉民事活動,須有充足理由謹慎為之,至少應滿足兩項條件:(1)僅賦予利害關系人申請權,不足以保護所有的利益主體。申言之,只有通過賦予檢察機關申請權才能彌補利益保護“真空”。(2)應嚴格限定檢察機關行使申請權的條件。現(xiàn)實生活中有時自然人長期下落不明,沒有利害關系人或利害關系人因各種原因不申請宣告死亡,致使權利義務不確定狀態(tài)長期存在,從而國家利益有遭受損害的危險。如失蹤人下落不明,其曾立有遺囑將全部財產(chǎn)遺贈給國家,而此時沒有利害關系人或利害關系人不申請宣告死亡,這時如不賦予檢察機關申請權,顯然不利于對國家利益的保護。當然自然人長期下落不明,使國家以外的利害關系人處于一種不利益狀態(tài),利害關系人享有是否申請宣告死亡的自由,而不能由他人或檢察機關“越俎代庖”。有學者認為“國家利益的損害為國家介入的唯一理由。失蹤人無利害關系人或利害關系人不提出死亡宣告,而不申請會造成國家、集體利益損害的,由人民檢察院申請。”[5]較為合理,只有在國家利益遭受損害時,才能賦予檢察機關以國家利益“代言人”的身份申請宣告死亡,以保護國家利益。《建議稿》第46條“下落不明的自然人無利害關系人或利害關系人不提出死亡申請的,應當由人民檢察院可以提出死亡宣告申請”,徐國棟教授主持的《綠色民法典》第429條規(guī)定“如某人消失且音信全無滿兩年,任何利害關系人或檢察院都可向法院宣告其失蹤”。
筆者認為,上述規(guī)定對于檢察院的申請權顯然賦予過寬,會導致對利害關系人意思自治的嚴重干涉,致使非國家利益以外私人權利義務違背當事人的意愿而發(fā)生變動,與民法私法之本質(zhì)不合,實無必要。
(二)由人民法院判決宣告
宣告死亡制度的適用將導致以被宣告人為中心的法律關系消滅,對被宣告人的利害重大,故不能由自然人或其它機關隨意為之,為確保其嚴肅性、穩(wěn)定性,只能由法院依法審查并以判決宣告。
人民法院宣告死亡判決中對于死亡日期的確定,《民法通則》無明確規(guī)定,《意見》第36條規(guī)定:“被宣告死亡的人,判決宣告之日為其死亡的日期”。學者們對此規(guī)定看法不一,支持者在比較幾個時間點優(yōu)劣后,認為“死亡宣告稱‘宣告’,當然應以判決宣告日最具優(yōu)勢,司法解釋之規(guī)定可資贊同”[6]反對者認為“它使得對于被宣告人死亡的時間可以由利害關系人來決定,極不嚴肅。它將被宣告人死亡時間統(tǒng)一規(guī)定為某一時間,忽視了被宣告死亡人下落不明的不同情況,以及有關該人在生理死亡時間方面所可能存在的差異。建議被宣告死亡人其下落不明滿4年之日為其死亡日期,戰(zhàn)爭期間下落不明,戰(zhàn)爭結(jié)束之日為死亡日期,意外事故下落不明,意外事故消失之日為其死亡日期。”[7]筆者認為,死亡日期的確定直接影響利害關系人的利益,如被繼承人的范圍大小,遺產(chǎn)的多少等。對死亡日期的確定要慎重衡量,應確定一客觀事實發(fā)生時間為死亡時間,盡量減少人為因素對日期確定的影響。通常下列時間點對于宣告死亡制度有重要意義:(1)最后音信之日(2)下落不明期間屆滿日(3)申請宣告死亡日(4)人民法院尋找失蹤人公告日(5)公告期屆滿日(6)人民法院宣告判決日(7)判決生效之日。其中(3)、(4)、(5)、(6)、(7)易受利害關系人或法官左右,被宣告人何時死亡掌握在他人手中,作為死亡日期不嚴肅,不可采用。應在(1)、(2)中選擇。德國、日本、我國臺灣地區(qū)采用(1),而意大利采用(2)。失蹤人喪失音信,長期下落不明,其可能死亡亦可能沒有死亡,如死亡其可能在無音信之日后的任一時間死亡,無法準確判斷。“客觀上,失蹤人已經(jīng)死亡的推定是隨著時間的持續(xù)進行而逐步形成的,實際生活中,有當事人對于失蹤人‘已經(jīng)死亡’的認識,只能形成并強化于失蹤事實的長期延續(xù)而非失蹤事實之發(fā)生。”[8]因此確定期間屆滿之日為死亡日期,既符合人們的心理習慣,又顧及對被宣告人利益保護,客觀上又避免人為因素左右,較合理。
同理,因意外事故、戰(zhàn)爭等原因被宣告死亡人的死亡時間均應為上述相應期間屆滿之日。當然,因為是推定,如有反證能夠推翻此推定時間,應以反證時間為準。
注釋:
[1]參見鄭沖、賈紅梅譯:《德國民法典》,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羅結(jié)珍譯:《法國民法典》,中國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俄羅斯聯(lián)邦民法典》,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9年版。
[2]梁慧星主編、中國民法典立法研究課題組編訂:《民法典總則草案建議稿附理由》,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徐國棟主編:《綠色民法典》,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年。
[3]史尚寬:《民法總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年3月第1版,第96頁。
[4]史尚寬:《民法總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年3月第1版,第96頁。
[5]尹田:《論宣告失蹤和宣告死亡》,載《法學研究》2001年6期,第94頁。
[6]張俊浩:《民法學原理》,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年10月修訂第3版,第105頁。
[7]張淳、吳強軍:《關于貫徹執(zhí)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若干問題意見中的若干瑕疵及補救》,載《南京大學法律評論》1998年,第138頁。
[8]尹田:《論宣告失蹤和宣告死亡》,載《法學研究》20001年6期,第95頁。
文檔上傳者
- 外宣翻譯美學論文
- 宣木瓜灰霉病防治措施探討論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