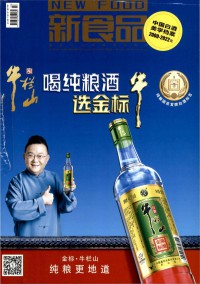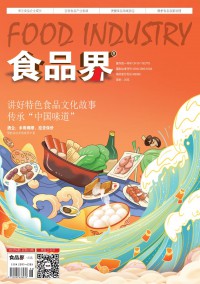食品問題論文:食品問題之倫理思索
前言:本站為你精心整理了食品問題論文:食品問題之倫理思索范文,希望能為你的創作提供參考價值,我們的客服老師可以幫助你提供個性化的參考范文,歡迎咨詢。

本文作者:楊光飛1梅錦萍2作者單位:1南京師范大學2南京曉莊學院
市場化進程中經濟倫理的“脫嵌”
從后果是否可預期性這個維度來看,食品安全問題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后果無法預期的,例如轉基因食品,這種技術創新到底是人類的福音還是災難,目前下結論還尚早,因而這種技術所帶來的后果可以說非預期的;另一類屬于后果是可預期的。我國近期所發生的大量有毒或者指標超標食品安全事件大都屬于后者。與非預期的食品安全事件相比,所謂可預期的食品安全事件,意即作為食品的生產商以及相關的責任單位(如技術鑒定單位、監管部門等)能夠預期到這種不安全的食品投放到市場之后的后果,但是仍然利用信息的不對稱,或者是出于利益、政績等因素而放松監管,讓問題食品流向市場,最終損害消費者的健康和安全。值得關注的是,表面上看,企業、商家為了牟取利益,通過使用不合格原料、添加不宜的防腐劑等方式最終讓問題食品流向市場,但是我們知道這和市場上充斥的一般的假冒偽劣產品不同,一般的問題商品往往會造成消費者經濟上的損失,而問題食品除了給消費者帶來經濟損失外,還意味著對消費者健康權利甚至生命權的侵害和剝奪。如果商家以及相關的責任單位能意識到上述后果,并站在潛在受害的消費者角度換位思考的話,在考慮相關的“成本-收益”之外,還應該自覺引入倫理的考慮,即他們應該意識到生產食品的目的不僅僅是一種經濟行為,同時還是一種倫理行為,即作為食品企業應該提供健康和安全的食品,這是必須遵循的道義行為,也是必須恪守的一種底線倫理,而生產和提供不健康和有毒食品顯然有悖于這種倫理底線。經濟行為中的倫理考量顯然正是經濟倫理學的重要議題,阿瑪蒂亞•森曾一般化地提出“倫理相關的社會成就觀”,認為這盡管并不能隨意消除社會成就評價中的隨意性缺陷,但是它可以使社會成就的評價更具富倫理性,而且必須使用更廣泛的論點和觀點來判斷什么是對“個人有益的東西。”[2](P10)市場本身受“看不見的手”的指引,是不講道德的,不會具有倫理偏好的,“帕累托最佳值只能定義經濟學的最佳值,但卻不能定義社會的或倫理學的最佳值”[3](P35);“資本主義是一種自由和工作的倫理,作為經濟協調的形式,它自己本身是不能創造和保持這種倫理的,”[3](P60)但是不講法治和倫理的市場是經不起重復博弈的,也無法建立起可持續的市場交易秩序。事實上,作為一種可持續的市場經濟制度,除了具備相應的法治條件,還應該需要相應的倫理基礎。正如美國倫理學家R.T.諾蘭在《倫理學與現實生活》一書中曾指出的:“每一種經濟制度都有自己的道德基礎,或至少有自己的道德含義。”[4](P324)西方的市場經濟體系盡管并不完美,但是迄今為止仍然是一種高效運轉的制度,并且總體上并沒有失范,這應該歸功于市場經濟背后的倫理基礎和法治條件,甚至有學者認為正是來自希臘的理性精神、希伯萊的宗教情懷以及古羅馬法律文化的注入,才導致西方的市場經濟仍然有序運行。對于市場經濟的運行,倫理相比于法律,是更為基礎性的東西,因為如果只強調法律的外在監督,而忽視經濟倫理的內在理念的培育,“這種基于計算的信任和依靠外在監督的法律會最終導致了商業機會主義盛行”[5](P281)。一種普遍主義的經濟倫理是諾斯所謂的“意識形態”,和法律的強制性措施不同,經濟倫理必須是“對相互權利的尊重,是一種內在監督,通過它可以形成一種有效的內在約束,以便防止各種損人利己行為的發生”[5](P283)。法律的外在約束固然能具有一定的制約性,但“本身不可能創造一個有意義的價值系統,倫理這一外在的價值體系卻可以通過價值內化形成一種內在的約束系統,從而使人們在遵從行為規范的同時懂得它的價值或意義”[5](P288-289)。市場經濟的運行需要一定的倫理基礎,也需要眾多利益共同體達成倫理共識。一種普遍主義的經濟倫理不僅可以帶來經濟意義上的節約交易成本,而且是市場經濟制度健康運行的基礎性秩序。在論述經濟倫理和資本主義的親和性關系時,韋伯認為,新教倫理的偉大之處,“在于沖破了氏族的紐帶,建立起信仰共同體與一種共同的生活倫理,它優越于血緣共同體,甚至很大程度上與家庭相對立”[6](P266),按照韋伯的闡釋,正是這種具備普遍主義的經濟倫理,才生成了資本主義,而市場經濟正是資本主義的核心要素。當然,這不意味著市場經濟僅僅只有新教倫理能充當倫理基礎,而只是說,市場經濟制度離不開經濟倫理的支持,從事實上來看,西方市場經濟制度運行有序的國家,除了宗教倫理的傳統,還有來自無神論基礎上形成的倫理共識。而我國食品安全問題恰恰透露出來我國市場化進程中尚未形成一種適應市場體制的普遍主義經濟倫理,出現了經濟倫理的“脫嵌”現象。“脫嵌”概念來自于波蘭尼[7]。在波蘭尼看來,市場以及經濟系統都是從社會、文化系統中孕育而來,在前資本主義社會,經濟是高度“嵌入”于社會中的,“(市場)在社會和文化標準中被置入的程度,社會和文化的副條件(價格系統就在這些條件下運行)的規模,在傳統社會中均高于現代社會。”[3](P8)隨著資本主義的到來,經濟才從社會中不斷分離出來,出現了不同程度的“脫嵌”現象,而經濟倫理的缺失顯然是這種“脫嵌”癥狀的表征之一。中國的文化傳統其實并不缺乏諸如“誠信經營、童叟無欺”這樣的經濟倫理,但一方面由于我國在歷史傳統上重農抑商,并沒有形成普遍主義的經濟倫理,另一方面,這種經濟倫理長期對應于鄉土中國的熟人社會,在引進市場經濟之后,對于急劇變革的市場轉型和社會流動,傳統熟人社會結構中孕育出來的經濟倫理無法與之匹配,導致舶來的市場經濟缺乏了倫理共識和倫理基礎,轉型以來的食品安全問題正是與此有關。
經濟倫理缺失的微觀視角:從企業到政府
近期國家質檢總局對食品安全的網上調查結果顯示:在“對當前食品安全形勢的看法”這一題項中選擇“問題太多,令人失望”的達51.36%,在“造成目前食品安全問題的主要原因”這一題項中,選擇“不法食品生產加工企業和個人利欲熏心”的占29.91%,選擇“對失信企業和個人的懲罰力度不夠”的占30.22%,選擇“執法部門監管力度不夠”的則占34.62%。[8](P10)上述調研數據一方面反映出消費者對于當前食品安全的不滿意程度,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消費者認為造成食品安全的主要因素是企業和相關的監管部門,在此基礎上,我們進一步追問,為什么在有法可依的情形下仍然有這么多的企業供給問題食品?相關的責任部門為什么監管乏力?事實上經濟倫理的缺失是一個潛在的重要因素,我們可以從企業責任倫理以及相關的監管部門行政倫理的缺失這兩個視角進一步加以剖析。首先食品企業缺乏對消費者健康和安全權益尊重的責任倫理。食品安全問題是在中國市場化不斷推進的大背景下發生的,食品安全問題甚至在有法可依的情形下仍然頻繁發生,愈益凸顯出經濟轉軌中的倫理緊張。具體而言,經濟倫理并不是抽象的,而且發生在具體的實踐中,在食品安全的諸多案例中,我們可以看到正是由于企業缺少責任倫理,企業實施機會主義,越過法律底線乃至倫理底線,嚴重損害了消費者權益。企業如果是通過技術改進等方式來降低成本、追逐利益,這本無可非議,這不僅有利于企業,也有利于環境和社會,會帶來雙贏和多贏的局面。問題在于,很多企業為了在市場中獲得競爭優勢,通過損害消費者權益的方式來提高收益。偶發性的食品安全問題,我們可以訴諸于個別企業或者商人的個體道德品質問題,普遍性的食品安全問題已折射出我們目前的市場經濟制度出現了經濟倫理的缺失現象,這種缺失首先表征為企業責任倫理的缺失,正如理查德•狄喬治所注意到的:“自由企業的惡,隨資本到中國也會發生”[9](P1)。其次還表現為政府以及相關職能部門行政倫理的缺失。一般意義上,行政倫理作為行政管理領域中的一種角色倫理,主要是人們關于行政活動對錯的判斷過程以及判斷的理由,涉及行政主體行為的正當性和合理性的一種判斷,即領導決策執行等行政管理活動的合法性問題。行政倫理和廣義上的經濟倫理是一種交叉關系,政府以及一些執法部門在對經濟活動的監管時也需要一定的倫理判斷,這不僅涉及到行政倫理,也和經濟倫理相關。近年來食品安全問題的涌現,除了食品企業沒有履行相應的倫理責任,政府以及相關職能部門也具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三鹿事件中,我們能看到地方政府及相關的職能部門不僅放松了日常的市場監管,而且在事發之后仍然考慮的GDP優先原則和地方、部門利益,喪失了公共部門應有的倫理判斷,更沒有履行起相應的職責。應該說,這種行政倫理的缺失有著深刻的背景。在中國市場化推進過程中,政府及監管部門受到經濟理性的裹挾,一味追求GDP,在日常管理中放松對食品安全、環境安全、生態安全的警惕,不再擔當公眾利益的保護人,而往往成了一些利益集團的庇護者。而按照公共經濟學的解釋,政府部門其實也是“經濟人”,有著自己的利益訴求,只不過在選舉制國家,政府官員為了爭取更多的選票,必須要考慮到公眾利益,所以在日常行動和行政決策中不能違背基本的行政倫理。而在我國當前,我們看到是另一種情形。消費者投訴之后,一些地方政府以及衛生部門借口各種理由,如以質監部門正在調查加以搪塞、加以推諉,“出了問題之后,這些部門互相扯皮,推卸責任,……一碰到有利益的事情這些部門都要管,一碰到沒有利益的就會把問題踢來踢去。”[10]正是由于在市場化進程中地方政府以及相關的職能部門一味追求GDP,形成了“逐利化”傾向,同時在這種行為的背后又缺乏一定行政倫理以及經濟倫理的制約,以至于這些部門并沒有結成一道道防護閥,一些相關的法律法規也難以真正落實。
經濟倫理缺失的后果及重塑路徑
食品安全問題的發生不僅僅是市場化本身帶來的,也不完全是市場監管制度的缺失帶來的,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市場中的利益主體、監管單位缺乏一定的價值理性和倫理底線造成的,因為缺乏倫理關懷的市場經濟會漠視人的生存、健康以及安全,也最終會導致市場秩序的混亂。只重視眼前物質利益而輕視經濟倫理培育的后果在我國已慢慢浮現出來。以食品中的奶粉業為例,隨著2008年眾多國產問題奶粉事件的逐漸曝光,消費者對于國產奶粉喪失了基本信任,導致了國內整個奶粉行業的萎縮和國外奶粉業的坐收漁利。食品安全事件暴露出來的只是“冰山一角”。質言之,引進市場經濟之后,我們充分重視了市場和形式法律的匹配性,認為沒有法律制約的市場經濟是無法持續的,但是沒有充分意識到,缺乏經濟倫理支持的市場經濟也會遭遇瓶頸。問題奶粉事件帶給我們一定的教訓:把經濟倫理的培育視為企業發展和地方建設的額外成本是短視的,忽視經濟倫理的后果會導致類似于問題奶粉這種事件的發生,最終會限制市場交易秩序的擴展和持續,因而經濟倫理的重塑對于市場秩序有著不可低估的意義。經濟倫理的重塑首先需要建立一個公正的制度環境。只有在一個公正的制度環境下,經濟倫理對于企業來說并不是一種成本,而是有潛在的“收益”,企業遵循經濟倫理所帶來的聲譽也會成為企業的社會資本;如果每個企業都這樣,眾多企業遵循這種倫理的結果必然也會帶來良好的市場秩序。但是,對于每一個企業而言,在存在博弈關系的市場環境中,公正的制度結構是個體企業遵循責任倫理的前提(在我國當前更是如此),否則,踐行即意味著需要多付出成本,在一定時點上必然會影響企業的利潤,這樣,如果存在不遵循“盟約”的競爭對手,企業就會實施機會主義,最終會導致經濟倫理的失效,即并不會自覺地尊重消費者的權益,也不會把倫理內化到相關的制度中,因而經濟倫理的缺失還是和我們當前的不合理的制度結構有關。對于我國目前的情形而言,已經出臺了不少相關的制度法規,這些制度法規的嚴格執行是企業和地方政府履行經濟倫理的重要條件。正如上文分析的,如果缺乏一個公平競爭、執法公正的環境,即意味著違背經濟倫理能夠獲取收益,而遵循經濟倫理反而會被逆淘汰,這樣即意味著不公正的執法環境會縱容更多敗德事件的發生,而在公正執法、公平競爭的制度結構中,敗德帶來的損失會遠遠大于企業通過敗德行為所獲取的收益。公正的制度環境實際上意味著敗德者會受到嚴懲,而守德者則會受到激勵,帶來的后果是企業不會通過敗德行為來超越競爭對手,而是通過技術改進、管理創新等路徑來提升自己的競爭力,顯然這是我們所期待的市場。經濟倫理的重塑還離不開經濟倫理和相關制度的銜接。很多人認為食品安全問題是由于食品市場缺乏有力的監管造成的,盡管我們不否認這點,但是我們知道僅僅依靠市場監管并不能杜絕食品安全問題。正如有學者指出的:目前對于食品安全的問題的解決,大多是從法律法規、行政管理的角度入手,但是,“任何一種法律法規的頒布與實施,任何一種行政管理政策的出臺,都是作為一種行為準則或者說是懲罰機制出現的,具有一定的滯后性,或者說,只有某種行為造成某種程度的危害時,法律法規、行政管理政策才會起到一定的抵制作用”[11](P9)。這一點我們從我國的食品安全事件看得很清楚。隨著市場經濟的深化,我們既需要進一步明確市場監管制度和問責制度,更需要將經濟倫理和相關的制度執行結合起來。對于企業而言,要“真正把倫理風險納入其高層決策系統和食品安全風險管理中,遵守道德指南,制定食品安全倫理決策的原則,充分考慮企業應承擔的社會責任,企業所擁有的基本權利和義務等問題,企業通過篩選倫理道德方面的因素對食品安全方面的影響,按照重要性和績效標準進行倫理決策”[12](P111);對于那些監管部門來說,我們也要進行制度創新,要矯正單一的只重視經濟指標的評價體系,要把是否履行監管職責和行政倫理納入評價體系中,并讓消費者積極參與其中,通過制度創新,我們創造一個信息充分、制度公正、評價體系合理的情境,讓經濟倫理的遵循者不僅不會付出更高的成本,而且也愿意付諸實踐。經濟倫理的構建還需要和我們的市場實踐有效結合起來。經濟倫理需要理論上的表達和辯護,例如對經營倫理、企業社會責任、財富倫理等加以探討,同時也需要參與到市場實踐中,和正在發生的一些社會事實進行對話,這一點我們做得還不夠。從目前來看,我國仍然把經濟倫理學作為一種哲學課程在講授,一定程度上脫離了市場實踐,并沒有真正融入市場中的責任主體,而從西方的一些經驗來看,經濟倫理學早已走出象牙塔,成為公共管理學院、商學院、經濟學院的兼修課程,并走進EMBA、MBA甚至MPA的課堂,讓這些經理人、政府官員意識到倫理風險的重要性以及經濟倫理和經濟收益之間的內在關聯,也讓這些決策者真正把經濟倫理作為需要考慮的政策參數,把倫理參數納入到企業以及政府的決策當中。另外,從長遠眼光來看,我們還要從社會和倫理的意義上來重視經濟倫理的培育。經濟倫理并不能完全迎合經濟利益,而必須要承擔一定的倫理功能,要超越功利主義的目標來重塑經濟倫理,這意味著我們不僅要將中國傳統的一些社會倫理思想進行“創造性的轉化”,同時還要汲取域外一些倫理資源,構建成中國情境下的一種普遍主義的經濟倫理,對不良市場秩序加以矯正,構建符合人們期望的“好的市場經濟”。當然,僅靠經濟倫理不可能矯正市場的所有弊端,但正如阿瑪蒂亞•森所指出的:由于倫理考慮影響了人類的實際行為,而影響人類行為正是倫理學的主要任務。[2](前言)對于經濟倫理學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