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nóng)村居民人口老齡化論文
前言:本站為你精心整理了農(nóng)村居民人口老齡化論文范文,希望能為你的創(chuàng)作提供參考價值,我們的客服老師可以幫助你提供個性化的參考范文,歡迎咨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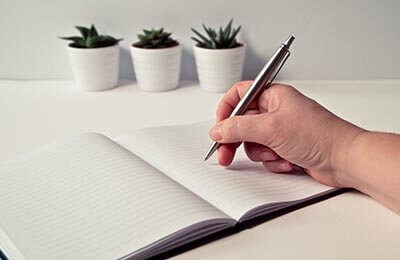
一、已成為“留守老人”的農(nóng)村老年人的養(yǎng)老
所謂留守老人,在某種程度上不過是空巢家庭的另一個稱謂罷了。只是空巢家庭這個概念的涵義更廣,任何一個核心家庭在子女長大成人后只要子女長期離家也就成為了一個空巢家庭。而所謂留守老人則不過是農(nóng)村空巢家庭中的老人而已,農(nóng)村家庭的子女進(jìn)入城市并大部分時間在城市生活而造成老人“留守”家園。如果要下個定義的話,似乎可以這樣來界定:常年居住在戶籍所在地、年齡不低于60周歲的農(nóng)村老人,且其子女及子女配偶常年不在身邊者。那么這樣一個群體在養(yǎng)老方面會面臨哪些問題呢?案例1:年近八旬的莊稼漢張老漢生于上世紀(jì)30年代,至今已年近八十,老漢家里有3個兒子。自上世紀(jì)90年代以來,3個兒子相繼南下廣東打工,其中小兒子通過努力在2005年左右終于自己翻身成為老板,在虎門自建了一家不大不小的制鞋廠。鞋廠的收益相當(dāng)不錯,張老漢的另外2個兒子也放棄了原來的工作而進(jìn)入其三弟的鞋廠。但是即便是在這樣一個家境富裕、兒女孝順團(tuán)結(jié)的家庭中,張老漢卻一直未放棄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雖然張老漢的3個兒子曾多次勸其父母放棄耕田轉(zhuǎn)而到城市去與他們一起生活,但每次都遭到老漢的強(qiáng)烈反對。
通過案例1的描述其實可以看到:首先是農(nóng)民的養(yǎng)老訴求較低。從單個個案得出的結(jié)論并沒有代表性,實際上,陳文娟[4]曾以規(guī)范的問卷調(diào)查方式對農(nóng)村居民的養(yǎng)老意愿進(jìn)行過專門調(diào)查,并指出農(nóng)村居民的養(yǎng)老預(yù)期總體并不樂觀,對養(yǎng)老問題的擔(dān)心較高。遺憾的是其調(diào)查主要是針對中年農(nóng)民,缺乏對老年農(nóng)民的調(diào)查。但是可以理解的是,在傳統(tǒng)家庭養(yǎng)老的觀念中雖然養(yǎng)兒防老具有很強(qiáng)的正當(dāng)性,但現(xiàn)實中年老一代對年輕一代的要求卻絕非不講人情。在多地農(nóng)村的調(diào)查中筆者亦觀察到一個有趣的現(xiàn)象,即很多農(nóng)村的老人與子女分居住在低矮的“老屋”當(dāng)中,其生活水準(zhǔn)明顯低于子女。但就是這樣的老人,對生活的滿意度并不一定就低。反而,只要生活能維持正常的一般標(biāo)準(zhǔn),做父母的更希望子女過得比自己好。這樣,社會保障在制度設(shè)計上可能會面臨一個問題,即農(nóng)村老年人認(rèn)同的標(biāo)準(zhǔn)低于社會認(rèn)同的養(yǎng)老標(biāo)準(zhǔn)。如此一來可能伴隨而來的問題便是農(nóng)民對社會養(yǎng)老保險的認(rèn)同度較低。筆者當(dāng)然不認(rèn)為既然農(nóng)民本身的養(yǎng)老訴求較低就應(yīng)該因此而設(shè)置較低的社會保障標(biāo)準(zhǔn),問題的關(guān)鍵是如何提高農(nóng)民的養(yǎng)老意識。
其次,農(nóng)民對作為財產(chǎn)的土地的認(rèn)識是影響其養(yǎng)老觀念的一個重要方面。正是因此,即便是家境頗富的張老漢也一直不愿意放棄種田。農(nóng)村土地的社會保障作用早已為學(xué)界所認(rèn)識,但是更為重要的是該從哪個角度去看待這個問題:有人因此而強(qiáng)調(diào)維持當(dāng)下土地制度的重要性,也有人強(qiáng)調(diào)土地的社保功能阻礙了土地正常經(jīng)濟(jì)功能的發(fā)揮。從社會保障的角度來看,農(nóng)民“戀土”而不愿離開土地,無非是因為心憂離開土地后生活沒有著落或者說“保障”,以至于不論土地收益高低,在未尋得城市立足之前是很難愿意棄土離鄉(xiāng)的。之所以需要土地?fù)?dān)當(dāng)社會保障的功能,不過就是因為與城市里的“單位人”相反,除了土地之外很難說還有什么可靠的依賴。這一點即便是國家大力推進(jìn)農(nóng)村醫(yī)療與社會保障的今天似乎依然如此。實際上,以上兩方面的分析反映的是同一個問題,即老年農(nóng)民表面上看來是因為觀念落后而出現(xiàn)不愿意參與社會養(yǎng)老并且對自己的養(yǎng)老狀況也不甚在意,其實際反映的還是他們對子女有無真正穩(wěn)定生活的擔(dān)憂。這種觀念或許顯得陳舊、保守甚至于在很多激進(jìn)的人看來是完全沒有必要的;但是無論怎么說,不可回避的一個事實卻是如果不能從制度上解決農(nóng)民向市民轉(zhuǎn)變的過程中建立穩(wěn)定事業(yè)以及獲得穩(wěn)固財產(chǎn)的可能性,而僅僅是企圖將適用于城市居民的社保體系擴(kuò)展到農(nóng)村的話,這樣的做法可能并不討好。畢竟,從個人的角度而言生活最大的保障只在于所在家庭是否建立在一個穩(wěn)定的事業(yè)基礎(chǔ)上。
二、即將成為“留守老人”的農(nóng)民的養(yǎng)老
留守老人是現(xiàn)階段已經(jīng)進(jìn)入60歲以上的農(nóng)村老人,那么比他們更小的一輩,即現(xiàn)階段年齡在50歲邊緣到60歲之間的農(nóng)民(學(xué)界通稱的“第一代農(nóng)民工”)則是可能很快就要成為“留守老人”的一代。據(jù)國家統(tǒng)計局的《2011年我國農(nóng)民工調(diào)查監(jiān)測報告》顯示,我國農(nóng)民工總量已達(dá)25278萬人,其中50歲以上的農(nóng)民工占14.3%,首次突破3600萬。然而,2011年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事業(yè)發(fā)展統(tǒng)計公報顯示,我國參加養(yǎng)老保險的農(nóng)民工人數(shù)僅為4140萬人,占比只有16%。盡管我國人口平均預(yù)期壽命已達(dá)74歲,50歲上下的人似乎仍未嫌老。但是作為主要在工廠或工地從事體力勞動的農(nóng)民工而言,進(jìn)入50歲以后顯然意味著進(jìn)入了一個體力衰退的高峰時期。那么這個群體面對的又是什么呢?
如果說對于60歲以上的“留守老人”而言,養(yǎng)老最大的障礙在于觀念問題的話,那么對于這些50多歲的老農(nóng)民或農(nóng)民工而言則面臨的困難要多得多。他們一方面面臨自己事業(yè)的轉(zhuǎn)折,即到底是回農(nóng)村還是留城市的兩難選擇;另一方面對于他們中的大部分而言,子女的問題可能仍遠(yuǎn)未解決。對于這樣一個群體,如果連最低的“社會保障”都沒有(事實上大多數(shù)確實沒有)則顯然有失社會公義,但如果說只要提高其養(yǎng)老標(biāo)準(zhǔn),每個月多發(fā)點保險金就能解決其“保障”問題,這恐怕亦只是天方夜譚。面對老齡化問題,中國的城市與農(nóng)村可能存在完全不同的狀況。城市或許還真能像一些樂觀的海外研究者指出的那樣,“城市化發(fā)展至少不會因為老年人口而面臨主要資源匱乏。相反,它們很可能會用一群活躍的或相對活躍的老年居民,能夠并且將為城市社會做出廣泛的貢獻(xiàn)而非依賴于城市。”相比之下,第一代農(nóng)民工的工作年齡即便再往后推延5年,在自身并無穩(wěn)定事業(yè)又缺乏社會養(yǎng)老保險的情況下,要使他們在社會生活甚至于消費(fèi)領(lǐng)域變得“活躍”或“相對活躍”怕也只能僅僅是一種美好的愿望罷!
三、結(jié)論與討論
對于農(nóng)村人口的老齡化發(fā)展趨勢,楊青哲[8]在其博士論文中做過詳細(xì)的估算。他以2010年全國第六次人口普查中關(guān)于農(nóng)村人口的相關(guān)數(shù)據(jù)做基礎(chǔ),預(yù)測了未來40年(2010~2050)中國農(nóng)村各時期總?cè)丝跀?shù)、少年兒童人口數(shù)、勞動力年齡人口數(shù)、以及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數(shù)。根據(jù)他的估算,即便是按照最高可能的總和生育率(2.3)進(jìn)行推算,農(nóng)村少年兒童人口和勞動年齡人口在未來40年時間內(nèi)將保持遞減趨勢,在2025年,65歲及以上人口數(shù)超過1億,到2040年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數(shù)達(dá)到峰值,約為1.5億。40年鄉(xiāng)村老年人口比重的變化,從2010年的10.06%上升到2050年的44.18%,共增長了36.33個百分點。這一變化趨勢必然導(dǎo)致社會撫養(yǎng)比的提高,楊青哲估計到2050年總撫養(yǎng)比將超過1。
很顯然,嚴(yán)重的老齡化會給整個社會養(yǎng)老體系帶來沉重的壓力。只有將自我養(yǎng)老(即依賴自身勞動收入的養(yǎng)老)、家庭養(yǎng)老與社會養(yǎng)老三者有機(jī)結(jié)合起來方能緩解這種壓力。這自然意味著要加強(qiáng)農(nóng)村社會養(yǎng)老體系的建設(shè),推廣并發(fā)展現(xiàn)有的新農(nóng)保制度,但圍繞老年人自身的勞動力再發(fā)揮及家庭養(yǎng)老支持在農(nóng)村而言卻才是具有最終決定意義的問題,因為目前新農(nóng)保制度的三大資金支柱乃是個人繳費(fèi)、集體補(bǔ)助與政府補(bǔ)貼,在大多數(shù)農(nóng)村地區(qū)集體補(bǔ)助所依賴的集體經(jīng)濟(jì)組織實際上已名存實亡,而個人繳費(fèi)情況也完全取決于家庭收入。而對于中國農(nóng)民家庭而言,家庭經(jīng)濟(jì)最大的問題是無法積累財富,可以說這才是農(nóng)民養(yǎng)老的死結(jié)。
因此,要加強(qiáng)農(nóng)民的社會保障,最有力的舉措還是在于持續(xù)提高農(nóng)民收入水平,并且同時進(jìn)行金融制度與土地制度的創(chuàng)新使得農(nóng)民的財富可以積累起來。實際上近些年來,國家越來越重視三農(nóng)問題,并試圖進(jìn)一步解決農(nóng)民增收問題,提出工業(yè)反哺農(nóng)業(yè)、城市反哺農(nóng)村,構(gòu)建城鄉(xiāng)經(jīng)濟(jì)一體化的政策主張。然而這些問題實際上都不可能在較短的時間內(nèi)得到較為全面的解決,同時即便農(nóng)民收入得以增加,但如果仍無法實現(xiàn)財富的積累,那么老齡化趨勢下的養(yǎng)老問題仍將無法解決。
作者:陳紅燕李靈孫守增定位器:長安大學(xué)出版社華中科技大學(xué)社會學(xué)系長安大學(xué)出版社
文檔上傳者
相關(guān)推薦
農(nóng)村工作會議 農(nóng)村工作意見 農(nóng)村合作醫(yī)療 農(nóng)村工作計劃 農(nóng)村工作總結(jié) 農(nóng)村普惠金融 農(nóng)村集中供水工程 農(nóng)村電商論文 農(nóng)村教育 農(nóng)村新農(nóng)村建設(shè) 紀(jì)律教育問題 新時代教育價值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