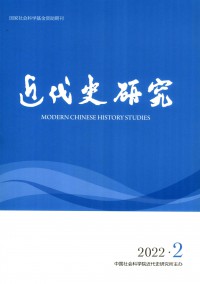近代江南農家生計和家庭再生產
前言:本站為你精心整理了近代江南農家生計和家庭再生產范文,希望能為你的創作提供參考價值,我們的客服老師可以幫助你提供個性化的參考范文,歡迎咨詢。

【內容提要】一個個有著獨立生計的家戶是土地占有和經營的基本單位,故農家生計的解釋對理解鄉村地權是一個不容忽視的視角。以往所謂“農家經濟”的研究,實際上是從經濟學的學科視野對農家生計做單一化的學科分析,離農民的日常生活尚有一定的距離。近代江南農民在狹小的家庭土地占有和經營規模條件下,普遍地選擇兼業,除經濟的考慮之外,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家庭人口的再生產需要和宗祧繼承的家族倫理觀念,溺女嬰就是一個典型地建立在文化習俗基礎上的經濟選擇。著眼于現代化理論視角的分析,其價值訴求隱含了更多的應然判斷,其邏輯是近代江南農民的經營方式不合理之處甚多,應該朝著合理的現代化方向努力。而在當時特定的社會歷史空間中,江南農民的家庭生計只能是這樣的一種境況。與農民的日常生活邏輯相比,學者的邏輯顯得十分蹩腳。
【摘要題】專題研究
【英文摘要】Everyindependentfamilyisafundamentalunitoflandpossessionandmanagement,therefore,explainingfarmer''''sbread-and-butterisaredoubtablevisualangletounderstandcountryownershipofland.Thereisactuallymuchdefinitespacefromfarmhousesustenancewhatsomescholarscall"farmereconomy"totheactuallivelihoodofpeasants.Inthescaleofhouseholdlandpossessionandoperationcondition,thefarmersuniversallyselectedpart-timefarming,besideseconomicalconsidering,apriorcauseconsistedintheneedofhouseholdpopulationreproductionandthesuccessivekinethics,addictingbabygirlwasnamelyatypeofeconomyselectestablishingonculturerite.TheagrariantypeofoperationinmodernJiangnanhadanirrationalityofsectionverymuch,itwouldbegivenupontorationalmodernizationheadingeffortwithaneyetomodernizationtheoryvisualangleanalyses,itsinformingimplicatesfartheraxiology,buttheagrarianfamilylivelihoodinJiangnanwasonlysuchasituationinthespecificsocietyhistoryspaceatthattimes.Thescholasticlogicappearsfullschlockcomparedwiththatofpeasants''''everydaylife.
ModeruChina/Jiangnan/Farmer''''sBread-and-butter
【正文】
一、從“農家經濟”到“農家生計”
要對農民的日常生活有一個正確的認識,首先就要真正地貼近農民,展示他們的日常生計,用農民自己的語言來說,就是“看一看人家一家一戶的日子咋過的”。目前中國農村社會經濟史研究領域普遍流行的概念是“農家經濟”,還不等于農家生計本身。因為所謂“農家經濟”實際是帶有方法論意義的學理概念,準確地說應為“農家經濟學”或“農家經濟的經濟學分析”,離真正的農民日常經濟生活尚有一定的距離。這一概念的解釋策略存在兩個問題,一是單一化的成本效益分析,二是價值預設的成分太濃,或者說以現代化理論的價值標準評價農家經濟的發展。這里看一下曹幸穗對1949年前蘇南農家經濟的研究(注:曹幸穗在時段限定上用了“舊中國”的字眼,我也不能同意,因為這會使自己在開始研究行程前就已經戴上了“有色眼鏡”,濃烈的價值預設有可能妨礙了對歷史真實的認識。),其中有一段對農民兼業化的評價特別具有典型意義。他從規模經濟的現代經濟學角度如此分析農民兼業化:“蘇南農戶的普遍兼業化,是小農生產與商品經濟結合這個特定的生產方式的產物。從積極方面說,農戶兼業化有利于利用農業剩余勞動力,增加農家收入和社會財富。”但是,農戶兼業化也會給農業生產帶來消極影響,概括起來說,它阻礙了社會分工的發展和形成適度規模經營,造成小農戶經營的土地資源的浪費,阻礙了先進農業技術的推廣,延緩了農業改良的過程(注:曹幸穗:《舊中國蘇南農家經濟研究》,中央編譯出版社,1996年,第233~234頁。)。可以說,曹幸穗的分析與珀金斯的“停滯論”、黃宗智的“過密化論”在本質上是一致的。研究農家經濟主要不在于如何評價,而是要探討農民們在特定的社會歷史時空中為什么會做出這樣的選擇,也就是說解釋要比評價更重要(注:與此相關的是學界對小農經濟的認識總也跳不出“評價情結”,小農經濟是經營形態層面上的概念,如從生產力水平角度給小農經濟定性,當然是可行的,但涉及到對小農經濟的評價,就有一個價值尺度問題,不可避免地會陷入一個價值預設的方法論誤區,不管是對其持肯定的或否定的評價均如此。關于正反兩方面的意見,可以參閱葉茂、蘭歐、柯文武的綜述文章(《傳統農業與現代化——傳統農業與小農經濟研究述評(上)》,《封建地主制下的小農經濟——傳統農業與小農經濟研究述評(下)》,《中國經濟史研究》1993年第3期。)。
從學術淵源上看,“農家經濟”的現有研究思路應追溯到卜凱的《中國農家經濟》一書。在該書中,卜凱提出了農家經濟研究的方法主要是通過制作表格進行調查,而“約有半數的表格系由本大學(指金陵大學——引者注)的高年級生所調查。其成績經審核后,予以相當的學分。其余之半數,則系由新聘之調查員所調查”(注:〔美〕卜凱:《中國農家經濟》,商務印書館,1936年,第2頁。)。費孝通在關于云南祿村土地制度的研究中對此種方法已提出質疑,認為農村社會研究中不宜采取這種方法,“一個和所要調查的現實沒有直接接觸的人,他不能發現這社區中所該用數量來表現的什么項目。他不能憑空或根據其他社區的情形來制定調查的表格。”而“一個社會學者去實地觀察一社區的活動,他的任務在于尋求人類社會生活中的基本原則。他不但是一種社會活動的記錄者,而且是一個解釋者。”(注:費孝通:《祿村農田》,載《費孝通文集》,第二卷,群眾出版社,1999年,第314~315頁。)社會人類學的社區觀察視角要比農業經濟學的學理分析更為深刻,也能更為全面、客觀地再現農民日常生活的真實狀態。調查表格或研究中所用的成本效益分析即使再精確,如果對農民日常生活的鄉土感覺甚為淺薄,那么這種定量化的研究也有可能遠離農民的生活實際,甚至其結論有走向謬誤的危險。或者可以說,基本假設是錯誤的,具體操作越精確,結論錯誤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相對于“農家經濟”概念,“農家生計”或稱“家計”能夠真切地反映農民從現實需要出發而做出的經濟、倫理選擇的合理性。要真正認識農民,首先就要理解農民,設身處地地考察農民生活于其中的社會歷史場境。當然,學者必須在農民社會關系網絡的動態系統中解釋農家生計,正如日本學者濱下武志所說:“能夠分析社會紐帶的線索,必須按照中國社會歷史的順序,研究集團與個人二者均包含在內的家族或地區社會的構成與結合、以家政家計等的家族為主的社會經濟活動、以及各行業的商業活動或經營哲學。”(注:〔日〕濱下武志:《近代中國的國際契機——朝貢貿易體系與近代亞洲經濟圈》中譯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第343頁。)既然在關系網絡中解釋“農家生計”,那就應當看到農民某種經濟選擇的文化倫理意義。從一般的方法論言之,如馬克思所說的,“在其現實性上,人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人與人之間的經濟交換關系必然有著倫理的、文化的內涵。在斯科特所說的“農民道德經濟”中,經濟的選擇常受著經濟之外的文化習俗制約。這在中國意義上,就是梁漱溟所講的“經濟、倫理相互為用”。林耀華在《金翼》中所描述的四哥志司,在抗戰后看到由于戰事、無休止抓丁派夫和攤派加劇了農民的貧困化,致使土地買賣、高利貸和抵押越演越烈,就考慮若一場戰火把他的店鋪毀于一旦,不如轉而用店鋪賺的錢在鄉間大量購進田地。此后數年間,他在黃村谷地購得一百畝地和多片山林,而店鋪生意和在土地上的田租收益又促使他再去放債。志司漸漸發跡了,但他利用苛刻的租佃與私人借貸方式沉溺于擴大土地之際,宗族鄉村人際關系原則卻被他忽視了,對此志留(即林耀華)也認為志司乘人之危以田做抵押是不道德的(注:莊孔韶:《銀翅——中國的地方社會與文化變遷》,三聯書店,2000年,第35~39頁。)。志司一切以經濟功利為目的,“掉進錢眼里了”,鄉人對他的道德評價降低,甚至親兄弟在道德上也不認同,這就必然減少了他在鄉土關系網絡中所能利用的人文社會資源。在吳江縣開弦弓村,有一種借貸互助會,“會員的人數從8~14人不等。在村莊里,保持密切關系的親屬圈子有時較小。因此,會員可能擴展至親戚的親戚或朋友。……被這個社區公認為有錢的人,為了表示慷慨或免受公眾輿論的指責,他們將響應有正當理由的求援。例如,周村長加入了十多個互助會,他的聲譽也因此有很大提高。”并且“這種互助會的核心總是親屬關系群體。一個親戚關系比較廣的人,在經濟困難時,得到幫助的機會也比較多。”(注:費孝通:《江村經濟》,江蘇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89~190頁。)周村長的事例與志司正好相反,但不管怎樣,即使是在經濟交換行為中,文化倫理的力量也不可小視。親屬血緣、婚姻關系與家庭生計的內在聯系也說明,對于農民的日常經濟生活僅做單一的經濟學解釋是遠遠不夠的。
美國人類學家孔邁隆(Cohen.Myron)20世紀60年代對臺灣南部客家“煙寮”(臺南屏東縣美濃鄭鎮的一個集落,以煙草生產為其主要特征,故作者以“煙寮”加以命名)的調查,發現該集落的農民大部分維持著大家庭生活。他認為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在煙草的耕作中,按照季節集中地投入勞動力是很有必要的,最經濟、最能確保家庭勞動力的方法就是維持大家庭。即使是分居另炊,只要在煙草耕作中共同使用家庭勞動力,就仍然是一個家,所以他把家計的分裂看作是分家的標志(注:CohenMyron.L:HouseUnited,HouseDivided:theChineseFamilyinTaiwan,ColumbiaUniversity,NewYork,1976.)。也許孔邁隆對于家計的解釋過于強調經濟因素,故有經濟學單一解釋之嫌。農家生計是農民家庭成員勞動協作的動態過程,家庭成員之間的角色關系就至關重要。20世紀40年代在陜北米脂縣楊家溝村調查地主家庭經濟時,發現地主破產的原因有三,即經商、吸大煙和經營不佳。由經商導致變賣土地的地主不少,如馬國干的兒子馬際選經營運輸業(趕駱駝),結果賠本變賣土地,導致家產大減。也有因經營不善而自殺或逼成神經病的。地主馬維新就認為米脂人不適合做普通買賣,只有放賬置地才比較適宜,做買賣用人不當往往是失敗的原因(注::《米脂縣楊家溝調查》,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0頁。)。羅紅光在最近的后續研究中發現,當地人所講的“生意”并非只是買賣,而是特指無論規模大小,生產和銷售渾然一體的一種勞動過程。馬家地主既繼承了山西祖先的生意傳統,又擁有綏德創業時的生意經,是該地出名的“口不讓人、錢不讓人”的大戶人家,故此“經驗的直接傳授方式既體現在操持‘家業’的日常生活的過程之中,同時也反映在他們言傳身教的‘家風’之中。”(注:羅紅光:《不等價交換——圍繞財富的勞動與消費》,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0~21頁。)父子兩代人的角色互動是家庭生計得以延續的人力資源條件之一,這是縱向的動態視角。從人口繁衍的角度看,“樹大分枝”,一個大家庭遲早要分家,分家是家庭再生產的基本方式,它通過重新分配原有家庭產權而使家庭再生產得以實現,也使家業得以縱向傳遞。
此外,在一個相對穩定的時段內,家庭成員角色地位、社會身份等對于家庭勞動的分工也是必須考慮的因素,比如關于婦女的社會身份、家庭角色、財產觀念的研究,對理解農家生計就是一個必不可少的環節。時下流行的所謂“女權主義”婦女史觀對于正確地理解婦女在家庭生計中的作用恐怕無積極意義。杜芳琴從學科本位意識和女權主義觀念出發,批判以往歷史學研究中女性意識的“缺席”,認為“只有具備了女性主體意識和歷史學的性別敏感視角,才能認識到史學中的女性缺失和歷史上對女性認識的偏頗,自覺擔當填補、重新評價女性的歷史的任務,為建構一部完整的男女共創、共處、共享的歷史做出貢獻;充分認識到研究婦女史不止是為學術,也是為婦女、為社會,也為男人,用自己的學術成果(書和教學)影響學界、學生,影響女性和男性,以期改變歷史沿襲下來的不利于兩性平等的性別觀念和性別態度及行為方式。”(注:杜芳琴:《婦女史研究:女性意識的“缺席”與“在場”》,載作者論文集《中國社會性別的歷史文化尋蹤》,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8年,第46~47頁。)如果作為一個從事實際工作的女權主義者,有這種理念應是值得提倡的,但學者畢竟與“婦聯”工作人員不同,主義之爭不能代替對現實(或歷史事實)的學術分析。我甚至懷疑,帶有強烈價值取向的女性主義婦女史觀是否必然導向性別關系的歷史真相?從婦女切入歷史,或從歷史場境中認識婦女,應強調女性社會角色在歷史時空坐標中的位置,以糾一般史學“性別歧視”之偏,似為正道。我那村上的農民常說:“這一家日子過得咋樣,娘兒們有一多半的份兒。”農民樸素的話語直觀、形象而又真實地反映了婦女在農家生計中的作用。
二、“兩種再生產”視角中的人地關系
近代江南鄉村土地占有權的總體趨勢是逐漸分散化,小農家庭勞動成為農業經營的主要形態。樊樹志認為江南地區地權的分散化進程實際上從明末清初即已開始,清中葉商品經濟的沖擊更加速了這一進程(注:樊樹志:《上海農村土地關系述評》,《上海研究論叢》1993,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3年,第110~111頁。)。清代前期蘇州府三家地主漫長的地產積累過程,就典型地說明地主占有一定量的土地與擁有分散小塊土地的大量個體小農同時并存。吳江縣周莊鎮沈氏家族,順治十六年(1659)由祖遺田產4.018畝起家,至道光三年(1823)的165年里,共在吳江縣購置田地596次,共4671.639畝,平均每次購置7.8畝。元和縣碧城仙館從乾隆十六年(1751)年至五十二年(1787)36年間,共置買田產51筆,計529.36畝,最多一筆為93.878畝,最少一筆為0.715畝。元和縣彭氏家族從乾隆三十七年(1772)到道光十七年(1837),置買田產24筆,共63.7192畝,最多一筆為20.842畝,最少一筆為0.252畝(注:分別見蘇州博物館藏《世楷置產簿》、《碧城仙館置產簿》、《彭氏“世祿挹記”置產簿》,載洪煥椿編《明清蘇州農村經濟資料》,江蘇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90~172頁。)。太平天國戰爭使江南地區人口銳減,大地產也受到極大沖擊。戰爭結束后,清政府召大量客民墾荒,一位當時的外國觀察者這樣分析道:“一八六五年以后,長江以南的土地為先來者占耕。他們耕種幾年以后,便發給他們一張地契,令完納田賦。在這種情況之下,當然只有靠田地生產而能維持生活的窮苦農民才能占耕土地,而且只是小量的土地。”(注:李文治編:《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一輯,三聯書店,1957年,第173頁。)曹幸穗的研究表明,進入20世紀以后,由于人口繁衍所帶來的人口壓力和商品經濟的發展,蘇南鄉村地權分散化程度進一步加劇(注:曹幸穗:《舊中國蘇南農家經濟研究》,第41~47頁。)。黃宗智也認為,商品和農業密集化帶來了近代江南農業生產家庭化的趨勢(注:黃宗智:《長江三角洲的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中華書局,1992年,第56~57頁。),這也是地權分散化的一個例證。既然學界前輩和同行已經對近代江南鄉村地權變動趨勢進行了相當出色的研究,我也就沒有必要再耗費筆墨了,只是想借此說明,在近代江南鄉村地權分散化的歷史進程中,眾多個體小農的農地經營規模必定十分狹小,地塊甚或相當分散,這對于農民生計的意義是不言而喻的。
20世紀30、40年代的一些鄉村調查,特別是陳翰笙所領導的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的無錫調查,總是強調土地占有的集中化與土地使用的分散化同時并存,以此說明當時土地制度的不合理。土地占有集中與分散的標準不一或研究方法不同,所得結論也不一樣。但無論如何,對于農地經營規模的細小化,時人一般是認可的。1933年春,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會在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無錫11村調查的基礎上,又進一步對孫巷、莊前、大鴻橋、北靡、廟庵、談家六村的農業經營進行了調查。韋健雄事后對三個村的材料進行了分析,發現“全部使用土地有80%左右屬于中農、貧農,他們每戶平均使用土地不到10畝;另一方面,地主富農使用土地只占20%。而且他們每戶平均使用土地也還不到20畝。”(注:韋建雄:《無錫三個農村底農業經營調查》,載薛暮橋、馮和法編《〈中國農村〉論文選》,人民出版社,1982,第487頁。)所謂的地主富農家庭土地經營面積也十分狹小,已經說明土地占有的集中化是不存在的。如果再將佃農的田面權認定為所有權性質,那么小農家庭農場土地占有權與使用權也并非是完全分離的。“滿鐵”上海事務所調查室1941年對無錫縣開源鄉榮巷鎮小丁巷、鄭巷、楊木橋三村75戶農家的調查也表明,經營土地5畝以上的只有4家,其余的71家全在5畝以下,其中經營1畝以下的甚至達13家(注:“滿鐵”上海事務所調查室:《江蘇省無錫縣農村實態調查報告書》,1941年,第90~91頁。)。“滿鐵”對松江縣華陽鎮裏行濱、許步山橋、薛家埭及何家埭四村落的調查,發現四村共63戶農家,有耕地548.59畝,平均每戶有耕地8畝多,4.9畝以下的19戶,78人,戶平均人口4.1人;5~9.9畝的18戶,72人,戶平均價格人;10~14.9畝的13,66人。戶平均人口5.1人;15~19.9畝的8戶,38人,戶平均人口4.8人;20畝以上的只有3戶,23人,戶均人口7.7人(注:“滿鐵”上海事務所調查室:《江蘇省松江縣農村實態調查報告書》,1940年,第38頁。)。在浙江省平湖縣,一般農家“均為小農,每家平均之耕地面積,尚不逮十三畝,而每家平均人口則在四人以上,以如此小面積之農地,維養多數之人口,蓋以農家缺少資本,則不能依勞力的集約經營。”(注:南京國民政府中央政治學校地政學院、平湖縣政府:《平湖之土地經濟》,平湖縣政府印行,1937,第82~83頁。)江南各地有關農地經營規模狹小的資料很多,恕不一一列舉。如此說來,農地規模狹小、又多小家庭,乃是近代江南農村人地關系比率的真實寫照。
至于小農家庭農地規模如此狹小的原因,恐不能從某個單一的因素來考慮。分家析產是家庭再生產的基本形式,從兩種再生產的角度看,它實際上是物質資料再生產與人口再生產相互作用的動態反映。費孝通從分家析產解釋農田的分散性,認為“每家土地面積窄小,限制了撫育孩子的數量。另一方面,土地相對較多的農戶生養較多的孩子,從而在幾代人之后,他們占有土地的面積就將縮小。在這些條件之下,人口與土地之間的比例得到了調整。”(注:費孝通:《江村經濟》,第138頁。)卜凱也認為,由于人口密度大,中國大家庭制度逐漸崩潰而趨向小家庭的轉化,在耕地總面積保持不變的條件下農場大小與家庭大小正能相互調整(注:〔美〕卜凱:《中國農家經濟》,第450~451頁。)。錢穆(籍貫為無錫蕩口鎮)回憶其年幼時家族各房支的興衰,記曰:“七房中人丁衰旺不一,初則每房各得良田一萬畝以上。繼則丁旺者愈分愈少,丁衰者得長保其富,并日增日多。故數傳后,七房貧富日以懸殊。大房丁最旺,余之六世祖以下,至余之伯父輩乃得五世同堂。……故五世同堂各家分得住屋甚少,田畝亦貧。自余幼時,一家有田百二百畝者稱富有,余只數十畝。而余先伯父及先父,皆已不名一尺之地,淪為赤貧。老七房中有三房,其中兩房,至余年幼皆單傳,一房僅兩兄弟各擁田數千畝至萬畝。其他三房,則亦貧如五世同堂。”(注:錢穆:《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三聯書店,1998,第8頁。)人口繁衍的自然規律所造成的家族內部土地占有的不均和貧富分化,正是通過分家這一家庭再生產的基本形式而使人口再生產和物質資料的再生產有機地統一起來。
在物價水平一定的條件下,一定面積的土地所能養活的人口應是個常數,故農家土地經營規模的狹小也限制了家庭人口的繁衍。在清代,蘇州郊區唯亭山鄉農村生活費用較低,“六七個制錢就可以泡一壺茶,三十個制錢就可以上一次蘇州去,人工又賤,租稅也輕,牲畜、農具又很便宜,雖然大都種的租田,但是有了七、八畝薄田也就可以維持一家的生活了。”(注:施中一:《舊農村的新氣象》,蘇州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刊行,1933年,第12頁。)據中華職業教育社1928年6月在昆山縣徐公橋所做的調查,“如用普通莊稼地供給五口之家,約須二十畝左右。”(注:楊懋青:《昆山縣徐公橋區鄉村社會狀況調查報告書》,載中華職業教育社編《昆山縣徐公橋鄉村改進事業實驗報告》,1928年7月,第23頁。)吳縣唯亭山鄉與昆山徐公橋鄉的畝制可能有差異,此外也不能排除民國初年物價水平提高造成一定面積土地所能養活的人口有所減少的因素。費孝通對吳江縣開弦弓村家庭人口與土地比率的人類學觀察也許更接近事實。開弦弓村農地面積為2788.5畝,有274戶農家,每戶平均約有10.06畝土地。“正常年景,每畝地能生產6蒲式耳稻米。一男、一女和一個兒童一年需消費33蒲式耳稻米。換句話說,為了得到足夠的食物,每個家庭約需有5.5畝地。目前,即使全部土地都用于糧食生產,一家也只有大約60蒲式耳的稻米。每戶以四口人計算,擁有土地的面積在滿足一般家庭所需的糧食之后僅能勉強支付大約相當于糧食所值價的其他生活必須品的供應。因此,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每家平均有四口人的村子,現有的土地已受到相當重的人口壓力。這是限制兒童數量的強烈因素。”(注:費孝通:《江村經濟》,第25頁。)一村之內土地面積不會增加,通過人為性抑制、溺嬰(尤其是溺女嬰)、出賣兒女等生育及非生育行為控制家庭人口,未嘗不可以看作是農民應付緊張的人地關系壓力的舉措。
李友梅于20世紀80年代中期對開弦弓村的口述史調查反映了經濟壓力和地方習俗對農民家庭生育行為的影響,一位農民這樣說:“通常,窮人家是用溺嬰來減少和避免貧窮的壓力,所以溺嬰在村坊上也是不遭職責的事。我鄰居家的媳婦第二始又生了個女小人,她婆婆當時就把這小丫頭放在馬桶里,后來這小丫頭被倒入的水淹死的。做娘的心里是舍不得的,但她曉得,孩子留下來反正也沒條件供她吃飽穿暖,養不活還不如死了的好。這樣想也就想通了。這里的人家只要有了兒子,一般只留一個丫頭,留兩個丫頭的人家是有別的打算的,多數是想用其中的一個去調換一個童養媳進來,因此許多童養媳還吃過婆婆的奶。窮人家頂多也只留兩個男小人,一方面缺少田地和房子,兒子留多了又負擔不起,另一方面鄉下人要考慮勞力和傳宗接代,還因為舊社會時孩子病亡率高,留一個兒子怕保不住。那些只有女孩子的人家,有的不愿招女婿,寧愿去領養一個男孩,這是從經濟和感情考慮,也是解決勞力問題的辦法。”(注:李友梅:《江村家庭經濟的組織與社會環境》,載潘乃谷等編《社區研究與社會發展》,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500~501頁。)三、農民家庭再生產的生活史解釋
狹小的農地規模使家庭勞動力相對過剩,農民不得不尋找農業外的就業機會,以補家用之不足。上海特別市社會局1920年的農戶調查顯示了郊區農家相當高的兼業比率,“蓋因居近都市,生活較高,往往受經濟之壓迫,陷于困窮,而上海尤甚。此次調查,無他項兼業者,百四十家中僅有十三,猶不及其十分之一。”(注:上海市社會局:《上海市百四十戶農家調查》,載馮和法編《中國農村經濟資料》,上海黎明書局,1933年,第242頁。)林惠海20世紀40年代初在吳縣楓橋鎮孫家鄉所進行的調查表明,該地農戶兼業也達到一定比例,在所調查的154戶農家中,家長兼業的有57戶,占37%(注:〔日〕林惠海:《中支江南農村社會制度研究》(上卷),東京,有裴閣,1953年,第64頁。)。該調查僅統計家長兼業情況,而未及其他家庭成員的兼業情況,如全面考慮,則兼業比率還會更高。如果說上述兩處地近都市,那么江南其他縣區的農家兼業比率也比較高。在常熟縣昆承區治安鄉,由于田少人多,每人平均1.6畝耕地,所以一般農民都有副業生產,據“”時蘇州專區農協會工作團的調查,全鄉共225戶,其中做成衣的144戶,木匠82戶,剃頭匠5戶,小販231戶,幫傭223戶,道士30戶,廚子22戶,鐵匠15戶,捕魚者11戶,其他26戶,副業收入約占總收入的25%左右,單純從事農業生產的僅23戶(注:蘇州專區農協會工作團:《常熟縣昆承區治安鄉工作總結》,1951年3月16日,蘇州市檔案館藏檔,卷宗號101—長期13。)。諸如此類的調查統計資料可以說不勝枚舉,只是說明江南農民兼業的普遍性,而要更深入地揭示農家生計的內部運作,還要進一步從農民的家庭生活史來解釋。
蘇南行政公署委員會主任歐陽惠林曾于1949年10月邀請了無錫縣梅村區四個鄉八位農民座談,調查農家租佃、債務情況,八位農民在座談會上生動、具體地談了自己的家庭生計。趙根大,大墻門十字鄉人,45歲,一家大小6人,妻子43歲,有勞動力,三個兒子(分別為16歲、14歲)一個女兒10歲。家中有自田7分(包括荒、墳在內),租田2.2畝(其中桑田8分),借種田一畝。養一頭豬、一只雞。當年養秋蠶半張種,12斤繭,曾買桑130斤,蠶種折4升米。據趙自己說:他并不欠債,因為人家不肯借給他,嫌他窮。每年的收入不夠吃,靠賣零工,每年要幫人家做五六個月的工。范壽根,住大墻門一保十一甲一戶,36歲。家中共5人,母親65歲,妻32歲,兒子7歲。女兒9歲。家里種租田三畝,自田九分(包括墳、荒、屋基),去年增加借田一畝(哥哥的田),另有房屋一間一架,羊一頭。本人共欠債15石稻。平時不夠吃,幫幫零工,過去原在滸墅關做席子,抗戰開始后,因為父親死了,才回鄉種田,附帶上街賣菜賣柴,來維持生活。薛永壽,周涇鄉第二保朱孔圩人,一家共6口人,母親60歲,由兄弟4人輪養,每年養3個月。妻39歲,小孩子4個。大的14歲,最小的1歲。家中有租田半畝,借田一畝半,其中半畝桑田。租田每年要繳租糙米四斗,借田繳白米一石。當年收秋繭12斤,換白米2斗多,仍然不夠吃。解放前幫人家開機船,每年一季4個月,可得五石米工資,又幫人家開碾米機,兩個月可以得兩石米。單泉根,周涇鄉第十七保四甲三戶,前單巷人。家中老小11人,嬸母50多歲,由他供養,有老父母。妻39歲,6個小孩,最大的14歲,最小的5歲。破屋三間。自田有5.2畝,租田二分半,租額每畝大米八斗,借田2.5畝,租額每畝大米一石,桑田有八分。當年養了一張秋蠶,家中勞動力很少,只有妻子可以幫助耕種,自己一年忙到頭,田總算可以勉強種下去。1947年因為腿生病,不能做生活,先后借了三石米與八石稻看病,利率50%。病好了,日子卻越過越難了。每年還租米、利米,剩下來的,就不夠吃。妻子從1948年冬天起,就到上海替人家做奶媽,月薪八斗米,補貼家用。吳新耕,住薛典鄉六保八甲二戶,42歲,有3子4女,其中兩個女兒已出嫁。自田2.5畝,租田7畝。每畝田收成白米二石,另外小麥每畝可收70斤,減去租額每畝五斗糙米、肥料(河泥)每畝折米三升,戽水費每畝二斗二升白米。余下總是不夠吃,每月食米要一石五斗,一年就要18石,再加苛捐雜稅,日子更難過。楊文彬,住薛典鄉一保七甲三戶,45歲。妻子49歲,有三女二男(大的17歲)。有自田1.3畝,租田4.5畝,借田3畝。每畝收大米一石八斗,繳租糙米5斗。收入不夠吃,要靠做短工。女人下田幫著種田。欠債40余石稻。因為種種原因1947年死了母親,借40擔稻,冬里標會還去一半,1948年嫁女,又用去20余石,仍是借的。同年把自田1.3畝、租田1.2畝賣出田面,得稻23石,還欠40石。陸金榮,梅村鎮第三保三甲三村人,40歲。母親已死,父親住大墻門鄉碩望橋黃家祠堂。妻蔡氏,有女三(分別為9、5、2歲)。自田一畝,租田2.75畝,另外尚有一畝是萬家祠堂的,不要交租,但每年要給祠堂350斤桑葉。當年養秋蠶一張帶3個圈。他自己兼做裁縫,每天可做3升米到4升米,每年約做70個工。謝桂泉,梅村鎮第五保十一甲十一戶高田村人,39歲,妻顧氏,女蕙芬12歲。家有自田1.7畝,其中桑田0.7畝,借田4.3畝,當年養蠶半張種。過去曾是制麻將牌的手藝工人,每年秋收后到城里去做工,第二年二月才回來,種田實際上只有4個月,調查時欠債兩石五斗白粳米(注:歐陽惠林:《無錫梅村區四個鄉租田債務情況調查》,載華東軍政委員會委員會編《江蘇省農村調查》,上海,1952年,第211~213頁。)。這八戶農家的耕地面積都不超過十畝,單靠土地甚至口糧都不夠吃,除吳新耕外,其他七家均不同程度地存在兼業現象。
另據1950年無錫市調查委員會的一份檔案材料,無錫縣西漳區塘頭鄉第五村金梅春,44歲,家有10人,有田17.6畝,自種9.1畝,不雇工,租出8.5畝,每年收租1石,農閑時兼做手工業,以土絲織成絲線出售,主要生活來源靠種田,“”中被評為半地主式的富農。與金梅春同村的馬來兵,32歲,全家6口人(妻、子二、女二),有自田6畝,灰肥田4.8畝,除1.5畝出租、每畝多收租米1.1石外,余均自耕,妻亦參加勞動。農閑以土絲做成絲出售,每年并雇女工一名幫助絲業勞動,時間約四、五個月,此項副業每年收入4.5石米,但生活來源主要是靠種田,“”時被評為手工業資本家成份,本人有異議。西漳區塘頭鄉范巷村人范福全,家中共有6人(包括妻、妾、子、女),自有稻田7.5畝,桑田1.1畝,租人3.5畝,轉租與人耕種,自田全部自耕,農閑時間本人出外做小工,另有小船一只出租,每月租金3石米,每年田中收入共4230斤米,小工收入2250斤米,船租收入5400斤米。“”時被評為工商業者,范福全本人在劃成份大會上也當場承認(注:無錫市調研委員會:《材料》,無錫市檔案館藏檔,卷宗號C6—長期—4。)。除金梅春家土地超過15畝外,馬來兵、范福全家的土地均低于10畝,家庭手工業在整個家庭經濟中占有相當比重。曹幸穗的研究表明,在1949年以前的蘇南農村,人口壓力的主要承擔者是10畝以下的農戶,其中尤以5畝以下的超小型農場為最甚,勞動力使用最節省的是16~20畝這一規模的農戶(注:曹幸穗:《舊中國蘇南農家經濟研究》,第112頁。)。據無錫縣農村工作團第五大隊1950年對該縣張村區寺頭鄉四個村一個保的調查,包括種菜、捕魚、養蠶等農村副業及農業以外的其他生產收入,在農民全年收入中占很大比重。從事副業生產的中農,其農業生產以外的其他生產收入可維持約四個月的生活,貧農可維持五個月,因此有些農民反而對農業生產不感興趣,他們這樣說:“種田是阿末條路,只要有點辦法,總勿會在家。”(注:無錫縣農村工作團第五大隊:《無錫縣張村區農村經濟情況調查》,載華東軍政委員會委員會前揭書,第96頁。)開弦弓村的兩位農民回憶1949年以前農業外就業對于貧苦農民家庭生計的重要性,其中一位說:“販運是本地不少人家維持生計的一種辦法,記得沒有戰爭時,開弦弓村在農閑季節有八十幾條船出去做生意,主要買賣青菜蘿卜、毛竹、海蜇和自捉魚蝦。窮人沒本錢做不起毛竹生意,大多只能在冬天做青菜蘿卜生意。做販運生意的人有時會遭到搶劫,弄不好還會挨打,因為那時到處有強盜,還有地頭蛇和賭輸場的人。他們知道你做了生意身上有錢就硬向你借錢,實際上就是叫你把錢拿出來給他們。”另一位農民還述及了他的家史,說:“我九歲(1913)死了父親。當時家里有三畝破田,在圩頭中間,一直積水,不能種麥,一年只種一熟稻。我兄弟兩個,哥哥在父親去世的當年結婚的,婚后不到一年就生了大病,他是因家里無錢不能上醫院而死的。隨之,他女人改嫁,母親到震澤鎮給人家做傭人,我出去做小長工,一家人各奔東西。我十八歲才回自家種田,母親也不再做傭人了,母子倆靠種三畝破水田,可一年的收入只有三擔米,連吃飯都不夠。為了生活,我在秋后農閑時與人家合伙租一條船到浙江沿海做水產買賣,比如買進新鮮海蜇,在當地用鹽腌起來,再搖回村里或蘇州等地賣掉,就靠這樣賺來的錢補貼家里的零用賬。可以說,不做點生意就活不下去,村上幾乎不見人家造房子,我家當時住的老房子還是在我祖父這一輩蓋的,估計有一百多年了。正因為這樣,一到秋里,村上的男人,特別是需要錢討媳婦的人差不多都走空了。我家窮,積錢難,我平時省吃儉用,不敢多花一點錢,婚事推遲到二十五歲才辦好”(注:李友梅:《江村家庭經濟的組織與社會環境》。)。所謂“貧農”,耕田大概總在10畝以下,此類農戶的家庭勞動力相對于狹小的土地來說有很大剩余,他們將相當部分勞動力投入到農業外的勞動中,精耕細作的集約化生產特點在這類農戶中已不再存在了。
所謂的地主、富農占有土地較多,按照“”時無錫縣政府劃分階級成份的標準,夠30畝地就應劃為地主。這部分農戶的農業生產收入除消費外尚有剩余,基本無衣食之憂,遂將農業剩余投向工商業(注:參見無錫市調研委員會:《材料》。)。據原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對無錫農村的調查,毛村在1936年以后有9戶地主富農開設粉坊,一般雇用工人10多人;東吳塘、龔巷兩村計有地主富農10戶開設酒坊,雇工亦有10多人。張塘巷村地主吳念生,一面收租一面投資開設醬園、米行,販運棉花、棉布,很快成為擁有千畝土地的大地主;毛村富農吳漢金從1931年開設粉坊起到1936年5年時間,除擴大粉坊經營外又買進土地40畝,建屋4間,買牛一頭。毛村吳桑根,1929年僅有1.2畝田,以后在城經商,陸續寄錢回家,放高利貸、買田、造屋,1948年已擁有土地36.2畝;東吳塘村工商業戶邵柏生,原只有一畝田,以販賣鮮魚為生,以后在無錫等地發展了百貨公司、紗廠、樂群書局等,從1929年起陸續在家鄉買地100多畝,“”時被評為地主(注: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原國立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無錫縣(市)農村經濟調查報告》,載陳翰笙、薛暮橋、馮和法編《解放前的中國農村》,第三輯,中國展望出版社,1989年,第307、319、327頁。)。從事該項調查的研究人員將這部分農家的經營活動解釋為地租、高利貸和商業資本三位一體,這也是以往學術界的普遍看法。這種解釋仍然是從固有的“地主制經濟”概念出發靜態地分析農家經濟過程。實際上,從動態的角度看,這部分富裕農戶的土地經營規模也有一個從小到大的積累過程,并且商業經營的風險性也有可能使其破產,此時土地的社會保障功能就格外突出。
無錫縣東亭區后旸鄉公益村人郭得元,全家15口人,其中11人在鄉下居住。1945年郭得元與次子郭儒國在無錫市南門外北長街20號開設“新得記”綢布莊,1949年歇業,“”時郭得元擺布攤。長子郭緯國為大龍布店小股東并兼職員,股金占十六分之一,因經營業外投機,虧了本,1949年布店倒閉,1950年“”時在家從事耕作。次子儒國因綢布店倒閉也返鄉從事農業生產。在農閑時,兩個兒子均往城協助得元經營布攤。女兒素琴在安鎮儲家巷國民小學校任教員,月薪得米八斗左右。該戶鄉間有平屋三間。土地32.025畝,內有4.77畝只有田底權,“”時被評為地主兼商人。郭得元自己說家中有老母、妻子等五人參加農業勞動,父子三人在農忙時輪流參加勞動。縣農村工作團的丁良典同志對他說:“縣府規定滿三十畝田即稱地主,不論人口多少。”該村貧農新桂仙向縣調研委員會反映,郭得元家在解放前雇用忙工一個,約60個工,由插稻起至養秋蠶止,臨時工約100個工,在農忙時郭得元與其子輪流回家勞動,但勞動時間不長,不如人家勞動力強,大都支配工作、算算工資。
無錫縣觀惠鄉河頭村人姚榮福,鄉下有稻田8.5畝,桑田2畝,屋基0.6畝,墳地0.3畝,秧田0.2畝;全家6口人,包括夫妻倆、祖父、兩子、一女。“”時只有祖父一人在鄉下,其余均住在市區。姚榮福的祖父原來經營煤炭業務,他本人也于1926年在無錫城內三里橋與別人合伙開設煤炭店,1928年拆伙,獨自在城內通志橋開煤炭店,當時資本為100元。這樣開了幾年,日軍占領無錫時,店內一切均被搶光,一家只得到鄉下種田。1942年姚榮福又遷至城內王道人弄開煤炭店,營業日益擴大,生計日余,就將土地讓其妹夫代為耕種,一家全遷至市區。1948年,姚榮福赴蕪湖一帶采購土煤。不久,因國民黨軍隊封鎖長江,煤船不能往來,并且一部分煤船半途失蹤,以致傾家蕩產。姚榮福急得生了中風病,在家不能走路,現欠人家約100余噸土媒,在1949年9月歇業。1949年3月將農村全部土地收回自耕,“”時被評為工商業家。
無錫縣梅村區周涇鄉十五保人郁鴻德,全家17口人,包括郁鴻德夫妻、三個兒子、三個兒媳、一個女兒、三個孫子、五個孫女,有土地24畝,其中佃入田1.83畝,借入田0.61畝,祖遺10.1355畝,自購田11.4245畝,完全自耕。自購田的過程是這樣的,1917年8月購田0.447畝,1918年8月購1.554畝,1921年4月購1.559畝,1922年3月購0.5365畝,1928年4月購1.06畝,1931年9月購0.65畝,1936年3月購0.7畝,1939年4月購2.159畝,1940年6月購0.274畝,1942年9月購0.764畝,1944年7月購0.525畝,1949年4月購125畝。1939年長子郁瑞卿一房七口遷至市區南門外清名橋下塘,與人合伙開設永生煤炭店,至1942年拆股獨資經營,當時資本計10石米,1949年解放后經營清淡。次子郁瑞臣,參加農業主要勞動,于農閑時做絲棉生意,掉換煤炭。三子郁瑞云,也參加農業勞動,1950年9月18日經介紹至友記鼎昌絲廠擔任助理工作。郁鴻德本人中年時擁有船一只,于農閑時運用少量資本販賣米糧,在抗戰前停止販賣,終年從事農業主要勞動。
華莊區太平鄉第六村陸子芬,1950年時40歲,全家共8口人,他本人于1937年與別人合股在無錫城南門清名橋上塘開設正昌布店,占四分之一股,1950年5月間因經營虧損、資金不足無法周轉,遂歇業。該戶鄉下有田11.7畝,其中押進田一畝,全部自耕,“”中被評為商人成份。
南泉區任港鄉人鮑淇康,全家10口人,本人原系布廠職員,1949年后失業回家從事農業生產。其兄鮑富康原開設小型腳踏機布廠,1950年因虧損解散。該戶共有田12.28畝,自耕9畝,出租3.2畝,兄弟未分家,自耕田由其妻及嬸母負責全部勞動,“”時被評為工商業者成份(注:無錫市調研委員會:《材料》。)。郭得元等數戶人家大都從事工商業經營,農業勞動曾一度在其家庭生計中退居次要地位,但是工商業經營的市場風險和戰爭的破壞,又使他們擺脫不了與土地的聯系,工商業一旦虧損、倒閉,他們還有土地可以過活。此外,家庭中的部分人口仍在農村居住,他們的“根”在鄉下,這當然并不僅僅是所謂的“戀土情結”,土地的社會保障功能恐怕更為重要。這使我不禁想起開弦弓村一位農民的話:“地就在那里擺著,你可以天天見到它,強盜不能把它搶走,竊賊不能把它偷走,人死了地還在”(注:費孝通:《江村經濟》,第129頁。)。
四、農家生計和婦女的家庭角色
研究農家生計還必須對婦女的勞動及家庭角色予以足夠的重視。李伯重主要以相當數量的地方志資料證明,“在清代江南農村,無論是在生產勞動中,還是在與社會生產有關的其他勞動中,農家婦女都確實起到了‘半邊天’的作用。”(注:李伯重:《“男耕女織”與“婦女半邊天”角色的形成——明清江南農家婦女勞動問題探討之二》,《中國經濟史研究》1997年第3期。)我對此基本同意,也不打算再做重復勞動,我只是要進一步追問,農家婦女在家庭生計中的心態變化和社會評價又當如何呢?單靠地方志資料根本無法回答這一問題,而民俗學和人類學家所留給我們的資料乃至方法則足以勝任。在近代江南農村,婦女是家庭紡織業和蠶絲業的主要勞動力,部分歌謠反映了農家婦女的這種勞動角色。清代道光年間松江府上海縣塘灣鄉有一首民謠曰:“織布女,首如飛蓬面如土,軋軋千聲梭若飛,手快心悲淚如雨,農忙佐夫力田際,農暇機中織作苦。”(注:何文源等纂:《塘灣鄉九十一圖里志》,下編,物俗,清道光十四年(1834),轉引自戴鞍鋼、黃葦主編《中國地方志經濟資料匯編》,漢語大辭典出版社,1999年,第1170頁。)江陰有民謠云:“新起房屋出角梁,當中有個織布娘,一天從早做到晚,還要延長到五更!”(注:顧頡剛等輯:《吳歌·吳歌小史》,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455頁。)織布之苦反映了農家婦女所承擔的家庭勞動甚或超過男子。清代文人王有光記錄了一首青浦、嘉定一帶的諺語,曰“紡車頭上出黃金”,并解釋道:“紡車,古時用以繅絲纑,后世更有棉花成紗,皆由車出。其器甚微,而其利甚薄,一家內助,以濟食力,此猶未足稱出黃金也。此而績之,為布為繒等物,足以衣被天下,婦習蠶織,不害女紅,不擾公事,不致舍業以嬉,浸為風俗,不啻黃金遍地”(注:王有光:《吳下諺聯》,中華書局,1982年,第77頁。)。這一解釋主要是經濟因素之外的社會倫理評價,但也足以說明農家婦女紡花織布對于家庭生計的重要性。當然,經濟變遷的因素仍在起著基礎性作用。20世紀前半期江南地區的工業化進程在很大程度上排斥了家庭棉織業在家庭生計中的傳統地位,例如,在寶山縣,“織布本是中小農的主要副業,收入頗大,所以織布的土地,大家都把它叫做‘聚寶盆’。若家有一架土機,每日織‘套段’,可成二匹,織‘長稀’至少可成一匹,大套六日可成一匹,每日約可賺錢二角。所以,農家平日常有機杼之聲,如同常有小兒哭聲一般,視為興旺之家。娶來兒媳,能從清早到午夜,手不停梭,便深得翁、婆、丈夫之歡心,和鄰里之稱道。但在今日,土布的銷場,全被洋布侵奪去了。‘聚寶盆’已一無用處,貼了工夫還虧本。家家都把布機、紡車停止起來,藏到灰塵堆里去了。因之多數女人,都拋下梭子,去做‘男人家’的事,即使長工,當‘腳色’,而男人們的勞力反轉漸感多余無用起來。”(注:陳凡:《寶山農村的副業》,《東方雜志》,32卷18號,1935年9月,轉引自章有義編《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三輯,三聯書店,1957,第648頁。)由市場體系變動所致家庭織布業的衰敗,直接改變了農家婦女的生存空間,而就業機會總是一定的,這就引起勞動力資源配置的社會性別沖突。
相對于家庭織布業,蠶桑業在近代江南農村更為普遍。在吳江縣開弦弓村,蠶絲業在家庭經濟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養蠶技術成為考察兒媳婦的一項主要內容,已演化為一種地方習俗。蠶養得好與壞,關系到新媳婦的身份地位,也影響到娘家聲譽。無錫有歌謠如此唱道:“四月里來暖洋洋,大小農戶養蠶忙,嫂嫂家里來伏葉,小姑田里去采桑;公公街上買小菜,婆婆下廚燒飯香;乖乖小孫你莫要與媽媽嚷,養蠶發財替你做新衣裳”(注:顧頡剛等輯:《吳歌·吳歌小史》,第501頁。)。歌謠反映了家庭成員之間的勞動分工,可以看出兒媳婦在養蠶勞動中是主要的勞動力。又有俗諺曰:“好女不著嫁時衣”,言女子出嫁至夫家,勤勞操持家務,自能“衣錦榮華”(注:王有光:《吳下諺聯》,第40頁。)。民國初年機器繅絲業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對農家蠶桑業形成一定的沖擊,但也增加了農家婦女的家庭外就業機會,同時自然提高了婦女在家庭中的地位。開弦弓村一位在村中絲廠工作的女工因為下雨時丈夫忘記給她送傘,竟會公開責罵她的丈夫。費孝通據此分析道:“這是很有意思的,因為這件小事指出了夫妻之間關系的變化。根據傳統觀念,丈夫是不侍候妻子的,至少在大庭廣眾之下,他不能這樣做”(注:費孝通:《江村經濟》,第165頁。)。無錫有一首歌謠如此反映婦女的打工生涯:“湖絲阿姐上工廠,梳頭打扮絕漂亮,右手張去小陽傘,左手提起小飯籃,賺了銅錢養阿三”(注:顧頡剛等輯:《吳歌·吳歌小史》,第485頁。)。此種場境中的婦女地位的提高并不能從根本上改變婦女的社會身份。開弦弓村另有一位婦女,在結婚一年后去無錫的一家工廠做工,并和廠里的一個工人發生戀愛,廠方發現后開除了他們。這位婦女不得不回到村中,她的公婆一開始拒絕再要她,但后來又收留了她,準備將她另嫁他人。以便可以受到一筆錢作為補償。最后,考慮到她在本村絲廠里能工作的本領,公婆取消了原來的打算,待她一如既往(注:費孝通:《江村經濟》,第166頁。)。公婆收留這位兒媳婦并非出于人道主義考慮,而是將她作為掙錢的工具,但從另一方面說,該婦女在絲廠工作的技能又成為她重新獲得家庭成員資格的條件。在當時的社會歷史場境中,農家婦女要想獲得自己獨立的經濟自主權和社會身份,仍然是相當困難的事情。至于未出嫁的女兒,在家庭中的經濟貢獻與其地位也是不相一致的。清代昆山一首詩反映了農家女的養蠶勞動,吟曰:“東家女兒發垂靨,阿母喚來采桑葉。枝頭葉稀翠黛顰,心憂蠶饑畏母嗔。歸來飼蠶蠶不饑,三眠百日蠶吐絲。又恐絲薄織作遲,唧唧復唧唧,當窗織成匹。織成云錦五色光,可憐俱為他人忙!”(注:[清]張潛之輯:《國朝昆山詩存》卷30,《飼蠶歌》,道光刊本,轉引自洪煥椿編《明清蘇州農村經濟資料》,第635頁。)從財產分配的經濟預期來看,女孩子養蠶為家庭創造的經濟收益并不能為她提供獲得家產繼承權的資格,所以是“可憐俱為他人忙”。
黃宗智通過在松江華陽橋薛家埭等村進行的口述史調查,發現參加家庭勞動的農家婦女在階層上是有區別的。薛家埭的婦女,屬于有錢人家,不需要干任何農活,她們從未下過農田,即使是很輕的拔秧之類的活計也未干過,家里也雇人幫忙。南埭村的何會花和郭竹英,從婦女干較多農活的村莊嫁到南埭,結婚后繼續在田里干各種農活,甚至干插秧這一認為需要有最高技能、通常認為是男人專有特權的農活。黃宗智認為,隨著商品化農業的出現和手工業的發展,產生了婦女和兒童參加生產的要求,隨后帶來了農業與家庭手工業相結合的生產家庭化的趨勢。也就是說,近代江南農業的商品化是以小家庭越來越多地采用機會成本極低的家庭輔助勞動力,邊際報酬不斷遞減的生產系統為基礎的(注:黃宗智:《長江三角洲的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第54、56、91頁。)。對于黃宗智的口述史調查,我不僅不表示懷疑,反倒認為是可信的,但婦女勞動力的較多使用是否就是農業密集化的表現形式,還值得進一步討論。前文已通過個人生活史資料展示了貧困農家兼業化的普遍性,使用婦女、兒童勞動力恰恰是農業生產中勞動力投入減少的標志。對于經營工商業的富裕農戶來說,土地耕作甚或已成了他們的副業,婦女、兒童勞動力投入農業生產中,可以緩沖工商業經營的風險。在這兩類農戶中,農業生產的“過密化”恐怕是不存在的。特別是在地近城市的郊區農村,商品化程度較高,農戶農業外的就業機會多,農業生產中的勞動力投入相對減少,如“”前上海近郊的楊思區沈家宅村,男子從工從商者為多,婦女成為生產上的主要勞動力,在被調查的37個農業勞動力中,婦女32人,男的只有5人(注:中共上海市郊工作委員會:《上海市郊區總結》,1952年11月25日,上海市檔案館藏檔,載《檔案與史學》2000年第3期。)。看來,商品化導致“過密化”的觀點是不成立的,如果由商品化來觀察農家生計的變遷和婦女家庭地位、社會身份的變化,則是比較可行的解釋策略。
當然,社會經濟事實的解釋不是簡單的現象描述,我們必須透過現象來分析其本質。近代江南農民家庭再生產的基本性質仍然可以在事實評判的層面上加以認識,而前文所說的從現代化價值體系出發的評價則有失偏頗。日本學者西dǎo@④定生對明清時期松江府棉紡織業的研究,在方法論上就很有借鑒意義,他認為:“假如以農村棉紡工業為媒介,從類型上掌握的話,那么它就是以商品生產為目的,從十一、十二世紀開始產生,到十六、十七世紀時完成其發展的農村工業體制的新形式。產生它的母胎是土地制度的強大壓力,這個土地制度的結構不是作為所謂佃戶制度在地主階層以下形成,而是表現為高額租稅等,與中央集權的君主專制國家不可分割地聯系在一起的。并且,在這種土地制度下的農村手工業,以控制它的商業資本為背景,作為個體小農的家庭輔助手段發展成為了農村副業。況且這種農村手工業因為不會從土地制度下解放出來,所以始終是個體小農的簡單再生產,不會向前發展了”(注:〔日〕西dǎo@④定生:《中國經濟史研究》,農業出版社,1984,第329頁。)。農民家庭的簡單再生產性質,是由特定的人地關系壓力、土地制度彈性、市場交換關系等基本要素組成的社會歷史要素所決定的。盡管近代江南地區的商品化程度相對于其他地區較高,但農地規模較小的貧困農戶仍然是為維持生計而不是為市場而生產,土地規模、資金條件決定了他們不可能進行擴大再生產。“”時無錫縣坊前鄉中農徐阿錫、雇農徐老三對當村干部不感興趣,還異口同聲地對“”工作團說:“分田不分田沒關系,多貸點肥料是真的”(注:蘇南農村工作委員會:《無錫縣坊前鄉典型試驗初步總結》,錫山市檔案館藏檔,卷宗號B1-2-18。)。并不是他們土地太多,而是資金短缺,在原有狹小的土地上資本投入已經嚴重不足,簡單再生產的維持就很成問題。擁有土地較多的農戶,雖然從事工商業、高利貸經營,但土地的社會保障功能又使他們的“戀土情結”得以強化,工商業的擴大再生產也沒有太大的社會空間,經濟資源條件之外的分家析產、戰爭事件的影響也是制約這部分農戶進行擴大再生產的基本要素。農家生計是流動的,土地規模自然也是變動不居的,土地戶間交易遂頻繁發生,由此產生了貧富分化的社會分層效應。家庭成員的角色、身份也部分地取決于他們在家庭生計中的勞動貢獻,物質資料與人口的再生產有機地統一在農家生計的動態結構中。
文檔上傳者
- 溫州近代醫學探析
- 中日近代化分析
- 近代農村金融論文
- 政黨近代產生文學探討
- 近代美術藝術期刊插圖藝術研究
- 古代與近代武術變遷動因
- 加強農業近代化水平
- 鄂爾多斯地區近代移民
- 近代鎮集發展和變遷
- 近代農民離村和城市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