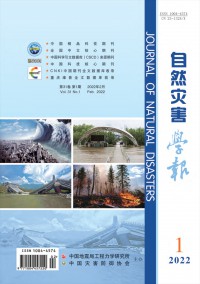略自然災害和民間信仰關系
前言:本站為你精心整理了略自然災害和民間信仰關系范文,希望能為你的創作提供參考價值,我們的客服老師可以幫助你提供個性化的參考范文,歡迎咨詢。

[論文提要]明清時期泉州自然災害頻發,主要有風災、水災、旱災、地震和鹽堿等。這些災害在自然、經濟和人文領域均造成了很大的影響。本文主要探討泉州地區自然災害與泉、臺兩地民間信仰特點之間的互動關系。為防范災害,泉臺兩地人民曾經尋求民間神祗作為精神支柱,因而兩地民間信仰有相近的特征。
[關鍵詞]泉州自然災害民間信仰明清時期務實性多元性難融性
本文所指明清時期的泉州地區是比較廣義的、包含地理與人文的概念,大致包括有泉州府(含永春州)、及下屬諸縣(含同安縣)。由于明清二朝泉州人民大量移居臺灣,所以將泉州與臺灣二府及光緒十三年單獨建省之后的臺灣作為研究的中心。泉州境內主要有泉州平原與戴云山脈、博平嶺等山脈;該地區背山面海,加之又臨近臺灣、澎湖等眾多島嶼,自然條件比較優越也比較復雜,是明清福建經濟發展相對迅速的地區。但是,這個時期自然災害頻繁發生,[1]給人民生命財產及各項事業造成極大的損失。并直接或間接地造成當地民間信仰文化空前繁榮,在人文領域產生了一系列的影響。本文著重探討兩者之間的互動關系。
一、明代泉州地區自然災害及其特點
1、水旱之災范圍廣泛,破壞嚴重
泉州地區水災頻繁,如萬歷十年(1582)八月丁巳,福建布政司奏:“四月多雨,水溢壞延平府衛城,沒侯官、晉江、南安等處田禾、民舍,人畜漂流無算,存者不能聊生”。[2]成化十八年七月甲午“永春縣大雨至八月丁酉,洪水泛濫,淤田疇,圮橋梁,壞官私序舍,濱溪民居淹沒尤甚,民亦有溺死者”。[3]成化二十一年,整個地區大面積水災,如志書所記:“自春徂夏積雨連月,晉江、同安、永春、德化、惠安五縣,田廬禾稼多為所壞。”[4]。萬歷三十一年(1603)八月丁亥“泉州府等處大雨潦,海水暴漲,颶風驟作,淹沒者萬有余人,漂蕩民居、物、畜無算”。[5]逾萬人遭滅頂之災,這在歷代的水災記錄中也是十分罕見的。萬歷四十三年(1615)八月壬午巡按福建御史李凌云奉命“勘過去歲八月由興、泉、漳三府水災情形,據實具奏,請將原題稅銀五萬兩或全或半存留賑恤”。[6]可見水災大量發生在萬歷年間。因此明代在泉州府及下屬各縣產生了一些影響比較大的主司防患水災的信仰神祗。又如旱災,成化十六年(1480)八月乙卯“免福建福州、興化、泉州、漳州府去歲秋糧”101400石有奇,鎮東等衛所子粒14800余石,“以旱災故也”;正德五年(1510)八月乙酉“免福建銀課一年,守臣以地方旱災為請,故有是命”。[7]終明一世,干旱成災的記錄較少。
2、泉州沿海颶風頻繁弘治六年(1403)七月初三日泉州大風雨,“自卯至申揚沙走石,開元寺西塔葫蘆傾覆,折林木無數。城鋪粉堞頹十之九,壞官私廬舍、商船、民船不可勝計”。[8]萬歷三十一年(1603)同安縣陡起颶風,海水漲溢“積善、嘉禾等里壞廬舍,溺人無算”。是月初五日未時颶風大作,海溢堤岸,驟起丈余,浸沒漳浦、長泰、海澄、龍溪民舍數千家,人畜死者不可勝計。甚至有大番船越過海堤漂入石美鎮內,壓毀民舍。泉州府鄰近各縣損傷十分慘重。[9]萬歷四十六年(1618)三月辛未方從哲報泉州風災:“昨日申刻天氣晴朗,忽聞空中有聲如波濤洶涌之狀,隨即狂風驟起,黃塵蔽天,日色晦冥,咫尺莫辨;及將昏之時,忽東方電流如火,赤色照地,廣頃西亦如之。又雨土蒙蒙,如土如霰”。[10]摧毀民舍若干,造成人員大量傷亡。萬歷四十六年(1618)五月庚子福建巡按崔爾進奏言,三月二十一日福建長泰、同安二縣大雨雹,“大如斗如拳,擊傷城廓、廬舍、田園、樹、畜”,壓死百姓220多人,請截留洋餉2萬兩以賑濟地方。[11]這是明代閩南見于文獻記載破壞最為嚴重的風雨雹災。足見明代閩南風災肆虐。
3、地震的多發地帶
閩南與臺灣海峽均處于地質斷裂帶,時常發生震災。如洪武二十七年(1394)四、五月,二十九年(1396)十二月,泉州連續發生地震。成化十六年二月丙辰,“福建泉州府地震,有聲如雷,屋宇皆搖。”宣德十年(1435)十一月癸未漳州府發生強烈地震:“日夜連九震,鳥獸之屬皆辟易飛走,山摧石墜,地裂水涌,公私屋宇摧壓者多,凡百余日乃止”。龍巖、漳平、長泰、南靖也發生了破壞力相近的地震。正德十五年六月庚甲夜,“福建福州、泉州二府各地震”。嘉靖四十三年(1564)正月癸巳朔“福建福州、興化、泉州三府同日地震”。萬歷二十二年四月壬戌“泉州府地震”。萬歷三十年(1602)正月辛亥“寅時,南澳同時地震,有聲如雷。蓋閩粵交界地也。”萬歷三十二年(1604)六月初八日、初九日泉州連續地震十余次,“山石海水皆動,地裂數處,郡城尤甚。開元寺鎮國塔尖墜,損扶欄。城內廬舍傾圮,覆舟甚多。”[12]這是當地極為嚴重的震災。萬歷三十年六月戊申福建興化、泉州同時地震。辛亥,“是日卯時福建福州府、興化府、泉州府同日又地震”。[13]萬歷年泉州進入地震活動期。由于地震所造成的空前破壞,加之突然襲擊,防不勝防,所以對泉、漳一帶民眾產生了極大的影響。恐懼之余,閩南鄉民也塑造了許多與之相關的神。靈頂禮膜拜。
4、瘟疫萬歷四十一年(1613)泉州“郡城大疫,人死十之七;市肆、寺觀尸相枕籍,有闔戶無一人存者。市門俱閉,至無敢出”。此外,德化還發生大規模鼠災,“田鼠害稼,一畝之田至有數千;春食秧,冬食谷,畔皆鼠道,草為不生。次年谷貴,人多饑死”。[14]道光《福建通志》卷五二載永樂十七年五月“建安縣張準言:建寧、延平二府自永樂以來屢大疫,民死”774600余口。瘟疫對社會、人口的摧殘極大,人們談瘟色變,因而在當地民間信仰中也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泉州地區瘟神崇拜盛行,明代泉州文人黃景方《溫陵舊事》就把瘟神稱作“五方瘟神”,以示其神通廣大,監領五方。謝肇淛《五雜俎》卷六“人部”二也有所記錄。他說:“閩俗最可恨者,瘟疫之疾一起,即請邪神,香火奉事于庭,惴惴然朝夕拜禮許賽不已,一切醫藥付之罔聞,不知此病原郁熱所致,投以通圣散開辟門戶,使陽氣發泄,自不傳染。而謹閉中門,香煙燈燭,莙蒿蓬勃,病者十人九死。即幸而病愈,又令巫作法事,以紙糊船送之水際,此船每以夜出,居人皆閉戶避之。余在鄉間夜行,遇之則經行不顧;友人醉者至,隨而歌舞之,然亦卒無恙也。”可見瘟疫造成了泉州人的極大恐慌,他們只好寄希溫于“出海”等驅神儀式。
二、清代泉、臺兩地自然災害的發生更加頻繁,破壞更加嚴重
這個時期泉州地區,包括臺灣府在內都進入了天氣異常、災害頻繁發生的階段。主要的災害種類如同明代一樣,但水災爆發的頻率及破壞的程度均明顯超過了前朝。
1、水災成為泉、臺兩地危害性最大的災害
順治初年,包括漳、泉二州也發生大規模的水災。慘烈之狀,令人無法卒讀。康熙三年(1664)六月二十六日“泉州暴風雨,水驟漲,自辰至申水高丈余,城市肆湮沒,溺死甚眾,三晝夜乃退”[15]康熙十九年(1680)興化災情嚴重,斗米百八十余錢,“民有餓自縊、投水死者。明倫堂施粥,分西、南廠簽給;南廠婦女幼丁,西廠壯男。初有三千余人,后八千余人,有死及生子廠中。督撫發銀八百兩到邑,一兩谷一石,扣米五斗,分上中戶采買”。[16]乾隆五年(1740)七月十二日巡視臺灣兼理學政楊二酉等奏,六月二十二、二十三日“兩日風雨交作,臺灣郡城內外吹倒房屋”57間,營房7間;諸羅縣“自二十二日起至二十五日止,臺風連作,縣城內外官舍軍民房屋均有損壞。其鹽水港、笨港二處,山水驟下,溪流漲漫,浸倒房屋二百余家。鹽水港倉廒盡行倒壞,被浸倉谷現在極力曬晾”。[17]乾隆八年(1743)八月初四日福建陸路提督武進升奏臺南城“六月初四夜戌刻狂風大雨,……本營及下溪水營各弁衙署以及營屋、塘房、望樓、旗桿等項雖多遭風雨吹淋倒壞者十中七八,而倒塌不堪者十中四五”。[18]乾隆九年(1744)十月二十九日福建巡撫周學健奏八月十六、七等日詔安、南靖及漳浦縣云霄,平和縣南勝,泉州府廈門“因山水驟漲,海潮上涌,有沖倒民房,坍壞城垣、堤岸、橋梁,淹溺人口之事”。[19]乾隆十年(1745)八月二十四日周學健又補奏:七月二十七日近城及東南低洼各村,倒壞民房1000余間;“城垣、學宮、營房、墩臺均有坍塌”。乾隆十三年(1748)九月初四日福建巡撫潘思榘等奏:“八月十六日秋潮盛漲,沿海許茂保洲田漫淹”4000余畝,浸坍佃民茅寮39間;泉州“潮汛甚大,又遇大風,沿海埭田沖淹一千五百余畝。并據兩縣均稱,前次七月內沿海被受風潮,正值栽插晚禾之候,俱已補種,今晚禾已吐花結穗,咸潮淹浸不能復長,現在分別撫恤”。[20]同年(1748)閏七月十一日巡視臺灣陜西道監察御史伊靈阿等奏:“彰化縣本月初二日半夜起至初三日酉刻風雨大作,山水驟漲,沿溪一帶田園、廬舍俱有損傷……被水各村莊沖倒瓦草房屋”共1800余間,共賑銀476兩;淹斃男婦18名口,“照例賑給銀兩,飭令收埋”。[21]乾隆十四年“十月初九、十九、二十二三等自閩省地方俱有颶風,聞得臺灣鹿耳門一帶擊破船只甚多,淹斃者不下一二百人,即澎湖、海壇、金門等處皆聞有船只打壞、貨物漂流之事”。同年八月二十九日馬爾拜奏:“七月十一日據銅山口委貞稟稱,亦于是日颶風狂雨至次晚方息。有廈門水師中營哨船一只在古雷地方打破,其本港采捕漁船及外來商船”,毀船數十只,淹斃30余人。[22]乾隆十五年十月初九日巡視臺灣江南道監察御史書昌奏:“八月初八、初九等日因雨驟風烈,田舍、人船復有損傷失事”;其中淡防廳屬田園內水沖者9甲5分、沙壓者9甲4分、倒塌瓦草厝231間;臺灣縣屬沙壓40甲9分、水沖143甲2分、倒塌瓦草厝35間;鳳山縣田園沙壓者12甲,水沖126甲,倒塌瓦草厝386間;諸羅縣田園水沖122甲、沙壓67甲、倒塌瓦草厝43間;彰化縣田園水沖312甲、糖部3半張、沙壓20甲、倒塌瓦草厝1513間。臺防廳所管鹿耳門汛遭風船20只、淹斃舵水人等共10名。[23]乾隆十九年(1754)五月四日福州將軍兼管閩海關事新柱奏:五月一日“同安縣溪水漲溢,城垣倒塌兩處”,淹斃27口、倒房1700間;另據喀爾吉善奏:“同安縣坍壞民房”1182間,“淹斃大小男婦”28名口;各縣水沖砂壓田畝自數畝至二三百畝不等。[24]從清代文獻記載看,當時對泉州各縣造成大規模破壞的首先應是洪水災害。因而泉州當地民間信仰中有相當部分神祗崇拜與防患水災有關。
2、風災上升為本地區的主要災害
泉州地處季風區域,夏秋二季時遭臺風、颶風襲擊。有關澎湖地區的風災及其相關問題研究,本人已有專文論述。[25]乾隆十五年(1750)八月臺灣大風,刮壞民房廬舍無數,擊碎商船100余艘,臺灣知府方邦基所乘之舟至南日島洋面舟毀身亡。方氏系七月戊辰登舟,八月乙亥自鹿耳門放洋,越己卯遭風,在海上漂流一晝夜后在福清地界的南日島沖礁,舟毀人亡。隨從21人中,僅4人獲救生還。[26]又如光緒四年(1878)臺灣府城(今臺南)“于四月二十一日酉刻突遭怪風”,所過之處屋瓦齊飛,古樹為拔,轅署照壁、旗桿坍折,署內房屋大半夷為平地,圍墻傾倒;“署東箭道內兵房倒塌公壓傷左翼練兵十六名。北城垛口摧坍十余丈。城內外民房當風過處多有倒壞,壓傷數十人,壓斃二人。”[27]嘉義縣于四月二十二日寅刻“大風陡至,縣署大門既署內房屋悉為平地,余皆倚斜;經查臺北、彰化、南投等處雖先后俱遭風雨,情形較輕。”。[28]光緒五年(1879)臺灣后山自九月二十二日起大雨狂風,連霄達旦,至二十五日始止。打馬燕等處所墾田園有沖去一半或七八分者,禾稻雜糧俱有損失,營壘公所率多坍塌。[29]光緒六年(1880)臺灣鎮總兵吳光亮報稱“山中南北三路,自八月十七日至二十二日風雨交作,二十三日異樣狂風”。[30]光緒七年(1881)臺灣、臺北兩府屬因被颶風大雨,致使鳳山縣大烏山地方溪水陡漲,淹斃番民10余口。淡水、新竹兩縣海邊草寮民房間有吹倒。宜蘭、基隆倒房傷人;七月初一日至初三日又遭颶風大雨,尤為猛烈,臺灣縣安平及鳳山、嘉義、彰化、恒春多受破壞,各口船只均有沖擊飄沉。[31]光緒八年(1882)閩浙總督何璟急奏臺島風災損失情況:“本年六月十六日起臺灣、臺北兩府屬大雨傾盆,加以臺風勢殊狂猛,接連數晝夜,以致臺灣府城及安平海口民房、兵房均有倒塌”。彰化縣城倒壞民房100余間,兵房30余間,城垣40余丈,炮臺1座。文武衙署間有坍塌,壓斃男丁2人。新竹縣城倒塌民房草屋100余間,大甲迫近山溪,水勢暴漲,灌入土城,沖壞草屋100余間。城垣衙署亦有倒塌,堤工潰決500余丈。鐵篾等薪多沖入海。[32]光緒十年(1884)閏五月十九日臺北、淡水、基隆、新竹同時遭風;“內地泉州府屬之廈門,于七月初一二等日風狂雨驟,木拔瓦飛,官署民房類多塌損”,中外船只沉失200余艘,淹斃多人。[33]光緒十一年(1885)七月十四、五、六等日福州、漳、泉、臺、廈各口,臺颶大作,拔木毀屋,傷損船只不少,為近十數年所罕見。[34]造成各地風獅、風神信仰盛行。
3、旱災在內地山區與沿海平原頻繁發生
清代福建特旱記錄共有8次,分別在順治五年(1648)、康熙四年(1665)、二十年(1681)、三十五年(1696),嘉慶二十五年(1820),道光五年(1825)、十六年(1836)、光緒九年(1883)。以康熙三十五年(1696)為例,有關府、縣志稱,泉州府的德化大饑。“乾隆二十二年春漳州大旱田無播種,二十三年泉州旱饑”。乾隆二十三年(1758)泉州因旱災造成饑荒,仙游“大旱,斗米二百余錢”。直至浙江平陽海運大米船只迭至,米價才稍漸趨平;七月臺灣府諸羅縣大旱。[35]因而各地民眾祭祀主司旱災的旱魃蔚為風氣。
5、泉州等地的瘟疫造成巨大的生命損失
順治九年(1652)正月,由于漳州潮水突漲5尺,鄭成功軍隊得以突入海澄。同年漳州城被鄭軍團團包圍,糧盡彈絕,以致“人相食,斗米值五兩”。至清軍解圍之時,在城內收得顱骨73萬;于是“疫大作,死者無數”。[36]乾隆十八年(1753)海澄爆發大規模瘟疫,“死者無算”;同年泉州府也有瘟疫流行,“至明年秋乃止”。[37]道光元年(1821)七月間福建全省瘟疫流行,患者均因吐瀉暴卒,“朝人夕鬼”,不可勝數。[38]因而泉州鄉民對于瘟神等神祗崇拜有加。此時泉州瘟神崇拜有所變遷。人們以為瘟神原系360名進士在明初屈死,上帝命其血食回方,泉州人尊稱為“王爺”,常見的有朱、邢、李、池、吳、范、溫、康、蕭等100多姓。當地送瘟神的主要方式是“出海”,即以木船滿載紙人、紙馬等諸多神像及各種貢品,向海中放行。石碼商民不惜花費“五六十萬巨金”制作用以敬神的木船,浩浩蕩蕩直抵臺灣西岸,臺島鄉民或將之迎送,或建廟祀之。正如曾任興泉永海防兵備道、后卒于臺灣道任上的周凱于道光十二年(1832)寫就的《廈門志》“風俗記”所言:“吳越好鬼,由來已久。近更惑于釋、道。一禿也,而師之、父之。一尼也,而姑之、母之。于是邪怪交作,石獅無言而稱爺,大樹無故而立祀,木偶漂拾,古柩嘶風,猜神疑仙,一唱百和。酒肉香紙,男婦狂趨。平日捫一錢汗出三日,食不下咽;獨齋僧建剎,泥佛作醮,傾囊倒篋,罔敢吝嗇”。周氏所言未免過于尖刻,但確實道出了明清時期閩南鄉民對災害的畏懼感和祈求神靈庇護的心態。面對災害的頻繁襲擊,明清各級官員也確實組織人力物力進行大量防災抗災和災后重建工作。閩南各地民眾也采取各種措施應對突如奇來的自然災害。 三、各級封建政府的賑災措施與災區官吏、百姓的祈福禳災
1、賑濟與安輯、撫恤災民
所謂賑濟,即封建政府用錢糧救濟災民。此前首先要對災情進行實地評估。同年十二月二十日大學士和珅等對閩南洪災有一個全面的奏報:“一疏稱石碼等一廳四縣,先經給過無力貧民倒塌瓦房”34868間,每間給銀5錢;瓦披8144間、草房10002間,照例每間給銀2錢5分;草披2175間,每間給銀1錢2分5厘;“淹斃男婦大口”1893口照例給銀1兩,男女小口981口每口給銀5錢。通共給過銀24625兩。[39]第二年福州將軍兼署福建巡撫魁倫核準勘明漳州府屬漳浦、海澄、詔安、龍溪四縣淹田902頃50畝,共應賑災戶16451戶,內大口共42192口,小口共32700口;并按“被淹田畝戶口實數散給一月口糧”。[40]這次水災后果極為嚴重,如《史料旬刊》第三十期所載,魁倫于乾隆六十年(1795)報:泉州一帶“春夏之交,米價日漸增昂。現在每石糶錢七、八千文不等,合銀五兩以外。即省城米價,每石亦在四千七、八百文,合銀三兩以外。且春日各處雨水頗多,麥收未免歉薄。現在早禾雖經插遍,而低洼處所,亦因雨多之故未見及時茂發”,鑒于閩南水災嚴重,造成漳泉二府乃至省城糧價爆漲,官府只得赴福寧府購入稻谷、薯絲,海運漳泉以期平抑糧價。
對于評估并未成災的破壞,則責令地方官自行修建撫恤,如嘉慶十九年(1814)七月十五、六、七、八等月“猝被風雨,經該道府飭據臺、鳳、嘉、彰四縣,鹿港、淡水二廳陸續稟報,內如臺、鳳、彰三縣,鹿港、淡防二廳禾稻并無妨礙。間有損壞官舍、營房、橋梁、道路以及房屋損壞之貧民已據該府查明,自行修理撫恤”。[41]道光二十九年(1849)七月初二至初九日,泉州府屬的晉江、同安、南安、廈門、馬巷及金門,漳州府屬的詔安、云霄等廳縣均發生嚴重水災。同安與詔安最為嚴重。同安縣“風雨交作,兼之溪流驟漲,海潮頂阻,以致低洼處猝遭淹浸,水深數尺不等”;被水淹倒民房3848間,內無力修復者1402間,由縣署捐給修繕費;城鄉淹斃大小男女54口,由縣給資掩埋。被水貧民1963名口“并經捐給口糧,現在次第歸莊,不致失所”。[42]官方賑濟措施在相當程度上使嗷嗷待哺、流離失所的災民安定下來,對于恢復農業生產有一定的好處。與抗災及賑濟災民活動同時進行的尚有各級地方官員攜同當地士紳百姓社會賢達的祈福禳災活動,容待下文論述。
2、蠲免與緩征所謂蠲免即免除賦稅徭役。明洪武初年下令凡遇災荒,須以實奏聞,不得隱瞞,按實災蠲免。洪武七年(1374)又規定蠲免條例,即凡水旱之處,不拘時限,只要勘查屬實,即可免除稅糧。此后一省或數省,或單免夏糧,或只免秋糧,遂成通例。清代災免推行于立國之初,但數量無定制。至順治十年(1653)才將全部額賦分為十分,按田畝受災分數酌免。受災八、九、十分免30%,受災五、六、七分免20%,受災四分免10%。之后蠲免比率不斷大幅增加,如雍正六年(1728)改被災十分者免七,九分免六,八分免四,七分免二,六分免一。具體做法一是查明應免錢糧數目,預期開單申繳藩司核實,然后發給各業戶收執,并告示百姓周知;二是蠲免積欠,在高壓政策下百姓難以拖欠賦稅,積欠主要是災害造成的。所謂緩征即指成災五分以上州縣可以緩征當年錢糧,順延至以后年份。迨至明清二代也時常采取此項措施。如康熙四十六年(1707)福建巡撫張伯行“題報臺屬亢旱請照分數免征疏”呈報臺灣府屬臺灣、鳳山、諸羅三縣,當年入秋旱情嚴重,又遇上臺風,經布政使金培生、臺廈道副使王敏政實地勘查,三縣被災田園25373甲,共請免當年粟30154石6斗;而且因“臺灣遠隔重洋,風信靡定,報災分數,案準部覆,不拘定限在案”。由于災民還要承擔“應征粟”107696石4斗,百姓不堪重負,臺灣府知府周元文、臺灣知縣孫元衡、鳳山知縣宋永清等吁請朝廷將臺灣縣應征額粟33545石3斗“于四十七、八兩年帶征”。清政府予以批準。[43]這些措施均在客觀上有利于災后民生的恢復。
3.從臺灣、浙江等地販入米糧以平抑糧價,撫恤災民
閩南因水旱災害造成的糧食短缺,一般是由糧商自臺灣、浙江、江西、廣東等臨近府、省購入糧食彌補。如《清高宗實錄》卷1480記乾隆六十年(1795)閩南大面積水災后,魁倫再奏朝廷:“據泉州府廈門同知及漳州府稟稱,泉州府城十四日米價尚在六千以內,十六日有臺灣商船販米三萬余石進口,米價頓減,每日糶米三千七、八百及四千文不等。廈門地方因石碼、海澄等處收獲較早,新米已多上市,無需來廈搬運。兼福寧府米船連艘踵至,米價亦減至四千以內。漳州府早稻亦已陸續收割,自十三日以后市價漸平,每石現賣四千上下。查自上冬以來貧民食貴已久,一時米價大減,輿情歡悅,如出望外各等語。同日又據派福寧府總運浙米之督糧道季學錦來稟,浙江頭起米船已入閩境之南鎮洋面等語,計日即可運到。加以早稻登場,糧價更當月減。”在專任督糧官員催辦之下,名地糧食調入泉州受災地區,糧價也得以趨平。道光《福建通志、臺灣府》表明朝廷對閩南災荒十分關切,特別是當臺灣亦遭災且無米可調運之時,更是嚴飭福建各府、州注意籌糧。如嘉慶元年(1796)上諭:“臺灣一歲三收,今北路嘉義、彰化等屬雖晚稻多有損壞,而南路臺灣、鳳山二縣受風較輕,地瓜、番薯等項尚可有收。當勸諭居民廣為播種,亦足以資民食。且風災過后,勤于耕種,來春仍可稔收。尤當及時力作,不可稍有怠惰。再福、興、漳、泉四府,夙藉臺米接濟;今臺灣既被風災,目下僅堪自給,明歲春收后或米谷充溢,可以運售內地,固屬甚善;倘無余米可運,魁倫等惟當于各屬豐收之處豫為籌備。并勸令百姓等撙節衣食,家有儲蓄,不可再將米谷釀酒花費,致鮮蓋藏,豫為明歲之備。”由于蔡牽集團的騷擾,臺灣海峽洋面屢發劫案,造成臺米難以輸入閩南以解災困,嘉慶十四年(1809)朝廷特此上諭:賽沖阿等稱“閩南漳、泉二郡,向不產米,全仰給于臺灣。從前商販流通,食貨贍足,皆緣商船高大,梁頭有高至一丈數尺者;又準配帶炮位器械,間遇盜船,克資抵御”;因蔡牽行劫,洋面不靖,“是以商販不通,漳、泉米貴之由在此。”可見臺灣輸入閩南的糧食在抗災渡荒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一旦臺米受阻,閩南即告糧荒。通過閩、臺兩地聯合抗災行動,兩岸人民加強了政治、經濟與思想文化的交流;這也有助于清代閩南地區的民間信仰在臺灣的廣泛傳播與深刻影響。
四、明清時期泉州、臺灣兩地民間信仰的若干特點
由于以上所論證的明清二朝泉州地區頻繁發生各種類型的自然災害,這種特殊的自然環境與人文理念造成同時期泉州地區豐富多采的民間信仰文化。因此這個時期也是泉州民間信仰的繁榮階段,而且決定了這個時期泉州地區的民間信仰不僅具有全國城鄉各地民間信仰的共性,即基本上與祈福禳災、防災減災有關;而且具有若干特性,即務實性、多元性與人性化以及難融性。以下分別述之。
1.泉州、臺灣地區民間信仰的務實性
面對層出不窮、接踵而來且破壞巨大的自然災害,在防災減災手段十分落后的明清時期,泉州民眾更是將祈求生存和發展的希望寄托于形形色色的民間諸神,因而體現出更多的務實精神。就以泉州民眾崇祀天后媽祖為例。由于明清時期中國又進入了一個災害活躍的時期,水旱頻繁,莆田在康熙初年的災情就十分典型。如余颺《莆變紀事》“水旱”篇說:“甲辰自春不雨至于夏五月,官民步禱靡神不舉。六月廾六日滂沱大雨,五晝夜不止。平地水漲丈余,廬舍漂流,無數居人攀木顛而處者。七日煙火斷絕,積尸溝渠。城崩者三十余丈。……七月二日海波怒發,崩堤裂港,迤東一帶數萬余畝盡為魚龍之窟。咸水入地,靡草不枯,又無顆粒之收。次年四月稍雨,五、六月又旱,斥鹵之田十荒其九。”在這種情況下,人們加倍地崇信天后媽祖,希冀媽祖能給閩南蕓蕓眾生帶來好運和生的希望。至康熙三年(1664),漳泉一帶與莆田地界災情更為嚴重:“春無雨,谷貴,每石一兩銀。四五月俱旱。五日十九日乃雨。六七月大水異常,城垣崩塌,石塞圮壞。八月初五日水災,漳泉更慘。衙后林學絢發心棄產,收埋餓尸及暴露棺柩;有來報者不論遠近,”均與土公攜具前往收瘞。但是當地災情益發嚴重,“康熙四年五月初一日道府廳縣亦行捐俸,并會紳衿士庶勸殷實者量力樂輸,在萬壽宮分給。男女數千人紛紛道路,形容枯槁,衣杉藍縷。少婦含羞手遮面而捉襟見肘;老人喘息,欲定神而前擁后推,扶掖而行,尚顛躓勉強進先仍落后。共放米四次乃止”。這一段時間水、旱災反復侵襲漳、泉、莆各地,康熙朝陳鴻邦《莆靖小記》“康熙三十五年,自去秋亢旱,至四月谷價涌貴四錢五分。四月初小雨,洋田可播,高田無水”;以至各地官員百般無奈,除了求助于媽祖,又告禳于城隍:“步行至城隍廟設壇。是夜微雨一番。廿六夜大雨一次,廿七日午刻大雨,又晴,溝河竟無水。……眾言須請黃石玄天上帝入城,可祈有雨”;多次祭神、反復折騰仍無濟于事:“百姓奉神駕至東門外,竟大旱。谷價每石至五錢以上,貴不肯祟;肉價每斤二分,賤無人買。奉祀大洋大所張公圣君于鳳山寺,用青白布制八角旌旗,次日小雨一番,次夜大雨二次,竟不濟”。無奈之下只得向富戶借糧:“各鄉頑梗,查有積谷之家,數十為群,登門強借;不從,則居然瓜分而去。谷價至六錢以上,諸貨皆賤,惟米獨珍。近城諸井皆干,水亦甚貴”。[44]類似情形,慘絕人寰,史不絕書。閩臺民間信仰受自然災害的影響所形成的務實性、功利性特征,筆者另文已有所論述,可以參閱。[45]
2.泉州、臺灣兩地民間信仰的多元性與人格化
泉州人民包括包括移居臺灣的泉人后裔在內,可以說將這個特性發揮得淋瀝盡致。出于對各種自然現象和自然災害的恐懼與祈求平安的心理,人們將眾多的民間神祗充分地予以多元化與人格化,也就是塑造多種分工不同的神靈,以應不同的防災禳災的需求。閩南與臺灣人民所信仰的諸神名目繁多,都特別具有人情味,就這一點而言,似乎與其他省份、其他地區有明顯的區別。凡是威靈顯赫的神祗,都會得到閩南信眾的虔誠信仰,信眾們往往要給他們配一位夫人,以慰藉神靈苦悶的生活。如果某神已經配有夫人,自然就應該有兒子,所以還要增添王子或公主等神像。是此,就把想像中神的生活完全加以人格化,也就是與人類的生活完全相同,是人神同格的具體表現。神的配偶有二種,一種是由男女信眾好心奉獻給神的配偶,一種是傳說中神本來就有的配偶。(1)奉獻的配偶,如城隍爺夫人,由于掌管一方平安的城隍爺威靈顯赫,信眾們為了討此神之歡心,通常都在城隍爺的后殿,供奉有城隍爺夫人。尤其是泉州的城隍廟,后殿更供有兩位夫人,分別標記為城隍大夫人和城隍二夫人。又如土地媽,土地公是人們所最敬仰、又是家家戶戶最經常頂禮膜拜的神,因此信徒們也為其配有土地媽。不過據傳說,由于土地媽不得人緣,所以原則上不將其配祀于土地廟中。只有特別同情土地公時,才配祀土地媽。再如西秦王媽,就是西秦王爺(即唐玄宗李隆基,閩南民間將其崇奉為戲神)的妃子,還配祀有公子。一般藝人為了能得好妻好子,往往要到這里來拜拜祈禱。(2)傳說中的配偶,如圣王媽,就是廣澤尊王(圣王公)的夫人。又如虺媽即保義尊王夫人,由于此神持別寵愛夫人,因而在祭典行列繞境巡行時,如果把夫人的神輿排在后面,就有惹起此神憤怒的危險;所以游行隊伍只好打破男尊女卑的舊習,把夫人的神輿抬在前面。又如太陰娘,即太陽公的夫人。又如閃電婆,即雷神爺的夫人。再如盤古媽,即盤古公的夫人。閩南及臺灣民間說法,廣澤尊王(圣王公)的圣公媽,乃是此神自己所娶的夫人。西秦王爺(唐玄宗)夫人,是否就是楊貴妃則不得而知。其他更有王爺夫人、靈安尊王媽、有應媽、大眾爺媽、開漳圣王夫人、三山國王夫人等。總之,閩南人塑造的神明特別具有人情味。
除此之外,為了使諸神不至于孤單,還有眾多配祀。也可以分為二種:(1)與祭祀神職務有關的配祀,如城隍爺的配祀,有文判官、武判官;馬將軍、牛將軍;延壽司、速報司、糾察司(陰陽司)、獎善司、罰惡司、增祿司;謝將軍、范將軍。除了以上各配祀神之外,還扈從有三十六軍將與七十二地煞等神兵神將。再如青山王的配祀班子,則同于城隍爺。又如掌管瘟疫的王爺的配祀,就配祀有6位司官。大眾爺的配祀,幾乎和城隍爺相同,只因為是陰司,所以祭典時無神兵神將,僅和平日所祭祀的崩敗爺神像有差別。福德正神的配祀為虎爺。司掌生育之神注生娘娘的配祀,按十二支配祀保母十二人俗稱“十二婆姐”,各神像都抱一個嬰兒。(2)與祭神史實和傳說有關的配祀,如天上圣母的配祀有千里眼、順風耳。關爺的配祀有關平太子、周倉將軍。開漳圣王陳元光的配祀有輔順將軍、輔義將軍。西秦王爺的配祀有田都元帥雷海青。佛祖釋迦的配祀有韋馱、護法、伽藍、監齋、十八羅漢。
此外還有挾侍,即站在主神左右的侍神。在佛教稱為“挾侍”或“脅士”,不動尊的挾侍是制咤迦、昆羯羅,釋迦的挾侍是文殊、普賢;道教也有挾侍制度,玉皇大帝的挾侍為太乙救苦天尊、雷聲普化天尊。此外擁有帝號的神祗還挾侍有劍藍、印藍,擁有王號的神祗則挾侍有劍童、印童;文昌帝的挾侍為天聾、地啞,臨水夫人的挾侍為左女娥、右女娥。這都是閩南民眾根據主神的史實與傳說而設置,信眾為提高主神的品位,并使其更加人格化,才分別給各神祗配以挾侍。如皇帝格的神,配以劍監、印監;王爺級的神,配以劍童、印童;元帥級的神,配以神馬、馬丁;觀音佛祖配以善才、良女;地藏菩薩配以左右佛童;祖師配以左右道童;婦女像的神配以左右宮娥,但僅限予妃以上的婦女像才能用宮娥,夫人以下的則不能稱為宮娥;注生娘娘配以提粉、提花、提匣、提鏡(即所謂香花女);魂身,配以金童(奴)、玉女(婢)。總之,明清時期的閩南信眾為了從信念上抵御自然災害的破壞,并修補以此帶來的精神創傷,不斷地塑造出多元化的眾神并將之人格化,以應不時之需。
為了祈福禳災和祭祀上的需要,閩南與臺灣的民眾還使用一種“分身”的方法,將閩南的神祗請到臺灣或閩南其他地方,以供信徒祭祀;他們把寺廟主神和同一神像并祀在一個神龕內,但有大小新舊等級的區別;此外神像的敷彩也有所不同。例如,媽祖像的臉如果涂紅就稱為紅面媽祖,如果涂黑就稱為烏面媽祖,這就叫做“分身”。分身的數目很多時,就分別把各神像稱為一王、二王、三王等;如果是女神則稱為一媽、二媽、三媽等。如果主神是男神就稱為“鎮殿王”;如果主神是女神時就稱為“鎮殿媽”。除此鎮殿王、鎮殿媽的主神之外,都可以應信徒之請被迎奉到信徒所臨時設的祭壇處,以便為信徒治病消災與降福,完成任務后再由信眾送回寺廟。由此可知,此類神祗的分身像,完全是為信眾而制作,不過只限于威靈顯赫的神才有分身像,因為只有這種神,信眾才肯來招請,有時一個神能擁有十幾座分身像。這主要是因為閩南各地災害迭起,民眾只得人為地給神靈分身,希冀在各地禳災。
3.漳泉遷臺移民的分類械斗與泉州民間信仰的難融性
福建文化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它的難融性,或稱之為文化的“碎化性”。盡管福建文化是多元的,但其中某些因素則如井水不犯河水,各行其是,互不滲透。特別在閩南民間信仰中能夠體現出這種典型的地域特征。明清時期頻頻發生的自然災害與人多地少的基本格局,迫使閩南民眾漂洋過海,去臺灣謀生。來自閩、粵兩地,乃至于閩南的漳、泉兩地移民,由于文化觀念上的差異而形成心理上的互不認同與嚴重對峙,從而導致依祖籍地而區分人群的分類械斗。“分類械斗”一詞為湖南籍官員、曾任臺灣鹿港廳同知的陳盛韶于道光六年(1826)成書的《問俗錄》一書中提出,實際上始自康熙中葉臺南的閩、粵移民之間為爭奪田地、山林、水源等自然資源而爆發的大規模械斗。其后波及在臺的福建漳、泉籍移民,乃至于在閩的漳、泉、莆等藉農民、紳士也大量卷入。曾任臺灣道的姚瑩坦言:“臺灣大勢,漳泉之民居十之六七,廣民在三四之間。臺灣之民不以族分,而以府為氣類。漳人黨漳,泉人黨泉,粵人黨粵,潮雖粵而亦黨漳。”[46]這里奇怪的是作為粵籍的潮州人反而認同閩南文化,所以在閩、粵移民械斗時,公開袒護閩籍移民。有時泉州一府各縣間亦有械斗,即“分晉、南、安、惠、同”。[47]正如陳盛韶所言:“鳳山、淡南粵人眾閩人寡,余皆閩人眾粵人寡”,但械斗中往往是閩人大敗,主要是因為“閩人蠢而戾”而“粵人詭而和”、“不拒捕,不戕官”。[48]這些習性對于泉、臺民間信仰的特征均有較顯著的影響。由于臺灣移民的祖籍地各不相同,因此語言、風俗、氣質也就互異。同鄉的移民團體就聯合起來開拓新的土地,并且為了擴張勢力范圍,就奉祀故鄉原有的神明;其目的是利用民間神靈信仰來加強內部團結,以便合力對付其他的移民團體。例如漳州人奉祀“開漳圣王”陳元光,而泉州人則奉祀“廣澤尊王”,客家人更奉祀“三山國王”等,在民間信仰中有一定的不兼容性與沖突性。由于自然資源的有限性,造成他們極力地排斥外鄉人。發展到后來,所有這些分類械斗并非是神明信仰之間意識形態方面的直接敵對,而是信眾利用自己鄉土的神明所進行的生存斗爭。
我們知道,最早移民臺灣的是福建泉州人,其次是福建漳州人,最后才是廣東的客家人,而祖籍漳州的占80%。所有遷來臺灣的三種人均具有強烈的鄉土觀念,于是乃演變成殘酷的分類械斗。這個問題可以追溯到康熙六十年(1721)漳州人朱一貴在臺南發動的反清復明起義,閩南人起而應之并遍及全島。這時居住在下淡水流域平原的粵人13大莊、64小莊,合計13000多人組織義軍,號稱“六堆義民”,以“擁清”為名與閩南人展開分類械斗。乾隆四十七年(1782)彰化縣荊桐腳大道邊上的賭場,漳泉移民在此豪賭,由于在賭博中發現有人使用“惡錢”(即劣幣),從而導致漳泉移民之間大規模的分類械斗,彼此互相放火殺戳。乾隆五十一年(1786)林爽文在臺灣組織天地會起義,由于他是漳州人,其部下也多是漳州人,因此清軍在募兵時僅限于泉州人和客家人。因而造成林爽文隊伍對泉、客人的村落大肆報復。道光六年(1826)四月,彰化縣東螺堡睦宜莊(今員林大饒)的客家人李通,由于偷了閩南人的一只雞而成為導火線,閩、粵人之間大打出手,互相縱火燒殺,分類械斗的范圍北到大甲溪之北,南到虎尾溪之南的嘉義縣。把臺島上下一時攪得天翻地覆,人人自危。
嘉慶十年(1805)十一月,海盜蔡牽犯淡水,并攻打位于臺南的臺灣府城。時鹿港理藩同知黃嘉訓擔心蔡氏寇擾鹿港,就招募兵勇合力鎮守港口。豈料所招鄉勇全是漳州人,而鹿港居民多系泉州人,故次年二月鄉勇入鹿港時,遂引發漳州人對泉州人的分類械斗。于是鄉勇以討伐土匪為名,對泉州人橫加殺戳。當地泉人幾乎陷入絕境,以致大量投海自殺。動亂之中,對方信奉的神祗便成了己方重要的攻擊目標,例如臺北漳泉人械斗時,泉州人便向漳州人的開漳圣王廟發動攻擊,搗毀廟宇,掠走神像,并且挖掉神像的眼睛和鼻子,藉以迫使漳州人屈服。泉州移民還搬出福德正神來尋找心靈上的慰藉。志書曾載:“臺北縣三峽鎮福安宮,主神福德正神。自乾隆五十年(1785)創建以來,神靈顯著。嘉慶年間,漳泉人分類械斗,神助泉人,于雙方嚴陣中,神憑童乩宣示:本神當出陣。次日果目擊漳人陣中,忽現二十一斗士,縱橫翻旗驅敵,致泉人戰勝云。”[49]此類神話顯系無稽之談,但說明了兩類移民文化的不兼容性導致了兩者之間民間信仰文化的排斥性與難融性。咸豐三年(1853)八月,臺北八甲莊的泉州同安人與漳州人合謀,企圖攻打萬華的泉州安溪人與晉江縣、南安縣、惠安縣等所謂“三邑人”并加以驅逐,不料卻招致對方反擊,使八甲莊陷入兵燹之中。同安人勢單力薄,落荒逃往大稻埕,同年十月再建新村落。之后又加入自新莊方向逃入的同安縣人,才逐漸繁榮而形成今日之大稻埕。就是由于泉漳兩府邑人世代的矛盾沖突,才使清末民初的大稻埕與萬華人的敵對情緒難以緩解。咸豐六年(1856)與九年(1859),新莊的泉州人、漳州人與粵人發生械斗,泉州人中的同安人避難大稻埕,得附近泉州人之助把漳州人和粵人驅逐出新莊,漳州人出逃對面的板橋,粵人則亡命中壢。[50]以上僅舉規模較大的分類械斗的例子。實際上整個有清一朝,臺灣及閩南的分類械斗是層出不窮的。臺灣的義民廟中,奉祀一些械斗中的喪生者,但是多為孤魂野鬼,他們暴骨荒野,后來多半被有應公廟收容。
甚至由于音樂流派的不同也會造成分類械斗之始作俑者。這就是起源于北管音樂團“西皮”與“福祿”兩派的紛爭。其由來始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有林文章音樂師自基隆雙溪來到宜蘭,在此開樂館收徒講授音樂。而此前乾隆五十一年(1786)即有宣墾社通事漳州人吳沙,善于與居住此地的山地民族平埔人等溝通,因而立志開墾宜蘭平原,他與當地土著逐漸將宜蘭平原開發成功。至此,福建漳泉移民與廣東移民陸續落戶宜蘭。由于吳沙祖籍漳州,因而在此定居者大多為漳籍移民。這些新來的移民青年多投奔林文章門下學習音樂。一時林氏名聲大噪。但到后來,該樂館竟分成兩派即“西皮”、“福祿”,且兩派對立日趨嚴重。原來福建地方的音樂大體上可分為“北管”與“南管”兩種。其中北管又分成兩派:一派的“弦仔”(胡弓)是用“提弦”和音箱(把椰子殼一剖為二)做成,另一派的“弦仔”是用“吊鬼仔”和竹子做成。前者奉祀西秦王爺,稱為“福祿派”;后者奉祀田都元帥,稱為“西皮派”。由于兩派對立嚴重,且競爭異常激烈,以致宜蘭地區的漳籍青年幾乎全部卷入是非的漩渦,互相傾軋,不斷打斗燒殺,對地方治安威脅極大。時至光緒年間,西皮派的首領簡木根之徒,與福祿派的首領陳寶永之輩,紛紛在各地挑起械斗,從宜蘭經頭圍一直波及基隆。宜蘭知縣林鳳章抓捕兩派頭目各數名,并問以死罪,兩派之爭才略告平息。日據時期又死灰復燃,尤以基隆最為激烈。[51]這種因閩南信眾崇拜不同戲神而造成血腥沖突,甚至綿延長達一、二百年之久的典型案例,實不多見。足見閩南文化因素中所蘊含的難容性是有其深刻的文化背景和歷史根源的;并且與清代閩南地區頻繁發生的自然災害有密切的因果關系。
當然,泉州地區的民間信仰主要還是體現了追求平安、祥和的色彩。如廈門何厝就有早年遺留下來的風俗,該村順濟宮主祀媽祖,據宮中人說,每年農歷的正月十六日,該村民眾組織媽祖游神活動,均由鄰近的關帝廟中的關帝爺前來“邀請”媽祖一起出游,因為在本地人眼中媽祖地位高于關帝爺。[52]這個習俗本身也充滿了節日的喜慶和泉州人民的詼諧、善良。
注釋:
[1]這個時期是我國科學工作者已經發現的三個重大災害群發期之一。即夏禹宇宙期(約4000年前)、兩漢宇宙期(公元前206年至公元220年)、明清宇宙期(公元1500年-1700年)和兩個較小的災害群發期,即清末宇宙期和20世紀60年代末迄今正在進行中的自然災害相對頻繁時期。參見高建國:《災害學概論》,《農業考古》1986年第2期;徐道一:《嚴重自然災害群發期與社會發展》,載馬宗晉等編:《災害與社會》,地震出版社1990年版,第295-297頁;任振球著:《全球變化---地球四大圈異常變化及其天文成因》,科學出版社1990。
[2][5][6][7]《明實錄類纂》“自然災異卷”,武漢出版社1993年版。
[3][4]黃仲昭:《八明通志》卷八十一“祥異、國朝”。下編第916頁。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8月版。
[8][9][10][11][12][13][14][15][17]][36][37][38][43]道光《福建通志》卷二七一“明朝祥異”,卷二七二“國朝祥異”;同治七年正誼書院刊本。
[16][44]海外散人:《榕城紀事》;余颺:《莆變紀事》,收入福建省文史館編《莆變紀事》,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11月版。
[18]][19][20][21][22][23][24][29][30][31][32][33][34][37][39][40][41][42]水電部水管司科技司編《清代浙閩臺地區諸流域洪澇檔案史料》,中華書局1998年6月版。第298、303、305、311、339、348、349、376、418、432頁。
[25]詳見徐心希:《清代澎湖地區自然災害研究》,《臺灣研究》2003年第2期。
[26][27][28]臺灣中研院史語所《明清史料》戊編第九本,中華書局1987年影印本。
[35]詳見乾隆《泉州府志》、乾隆《續修臺灣府志》“災異”篇。
[45]詳見徐心希:《閩臺民間信仰的功利主義特點探論》,《福建師大學報》1996年2期。
[46]姚瑩:《東溟奏稿》卷四,臺灣文獻叢刊第四十九種。臺灣銀行研究室編印。
[47]劉家謀:《海音詩》。見諸家《臺灣雜詠合刻》,臺灣文獻叢刊第二十八種。
[48]鄧傳安、陳盛韶:《蠡測匯鈔問俗錄》,“問俗錄”卷六“鹿港廳、分類械斗”。書目文獻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138頁。
[49]臺灣文獻委員會編《臺灣省通志》卷二“人民志、宗教篇”,1971年臺北版第四冊第276-280頁。
[50][51]鈴木清一郎著、馮作民譯:《增訂臺灣舊慣習俗信仰》“緒論、寺廟祭神之地位”,第11頁、第12頁。臺灣眾文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89年11月版。
[52]詳見陳衍德:《閩南粵東媽祖信仰與經濟文化的互動:歷史和現狀的考察》,《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6年第2期,第76-8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