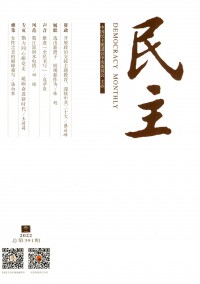民主憲政
前言:本站為你精心整理了民主憲政范文,希望能為你的創作提供參考價值,我們的客服老師可以幫助你提供個性化的參考范文,歡迎咨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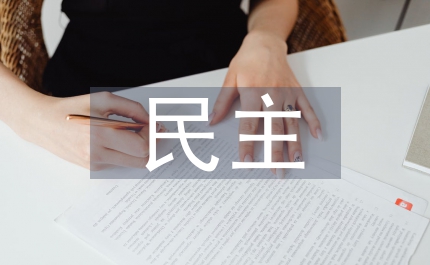
令很多人困惑不已的是:就在中國經濟以世界罕見的速率持續增長,許多領域都取得明顯進步的同時,全社會卻彌漫著一種躁動不安,仿佛危機將至的氣氛。有智者出來解惑,說這是由于中國經濟的發展回避了長期積累的社會深層次矛盾;矛盾沉積,形成潛在危機;于是出現發展與危機并存的奇觀。有人因此恍然大悟,有人卻更加糊涂:既然矛盾重重,怎么還可能快速發展?既已持續發展,怎么較之落后停滯的國家,如印度南美非洲,我們的危機感更加迫切深厚?
在任何社會制度下,社會與政府都是一對矛盾。社會所滋生的一切矛盾危機,最終的指向都是政府。政府要么解決這些矛盾;要么暫且壓抑,實際上是將矛盾吸附上身,集中起來。當這種矛盾的能量積聚到一定程度,就會集中爆發,與它的載體--政府同歸于盡。
不同的社會制度下,矛盾爆發的方式及其對政權的影響是大不一樣的。矛盾之所以構成危機,是因為它有能量。此種矛盾能量大致可分為三類:
1,體質性矛盾產生的能量:如經濟落后,資源貧乏;這都是社會本身體質不濟所形成的弊病,難以遽然改觀。
2,結構性矛盾:因為社會的組織秩序制度等等,不適應于變化著的現實,從而滋生的人與人人與社會之間的矛盾。
3,人們在現實中,對各種矛盾的感受情緒和態度,所產生的心理能量精神能量。
顯然,前兩種矛盾是第三種能量得以形成的基礎,但前兩種能量最終必須通過第三種能量才能爆發出來,產生作用;第三種能量能夠加強前兩種能量的作用力度。
在實行普選制的民主憲政社會,政權與政府是分離的。政府入股的是有限責任政府,政權與政府之間有著明晰的防火隔離墻。社會矛盾的積累爆發,只會促使政府下臺,權力易手;不會根本傷及政權,也不會破壞整個社會制度。同時,定期普選以多數形式表達的民眾自愿選擇的授權方式,給了社會矛盾所積蓄的心理能量一個遵循規范途徑發揮作用的機會。重新投票選擇執政者的過程,就是社會矛盾所積累的心理能量得到發泄釋放的過程。在此過程中,能量的渲泄依然遵循既定的途徑和程序,仍然受到整個社會制度和秩序的約束。因此,它是溫和的,很少破壞性的,一般不會演變成全社會的危機。選舉完畢,心理能量一般也就釋放完全--都是你自己的自愿選擇,有什么好埋怨的?還不滿意的話,下回再來吧--同時,社會成員重新選擇執政者的過程,同樣也是社會就解決體質性矛盾和結構性矛盾的執政方案重新作出選擇,再次達成共識的過程。在此過程中,社會關注的各項問題都會有一個令大多數人最為滿意的方案被選出;各方面都有所著落,社會趨于平靜。
社會危機演變成政權危機是傳統非民主社會獨有的頑疾。在傳統社會,政權所入股的是無限責任政府;政府由政權完全授權,擁有不受限制的權力。政權與政府兩位一體,同生共死。同時,社會矛盾所聚集的心理能量沒有根本性的正常渲泄渠道(輿論放開可起一些作用;但也可能起反作用。總之不能解決根本問題),它的爆發總是在矛盾忍無可忍,制無可制之際。因此,這種爆發必然是激烈的,充滿破壞性的。心理能量所引發的社會危機總爆發,不但能摧毀政府,摧毀政權,往往同時還要摧毀政權所維護所配套的許多現有社會秩序和制度。
社會組織秩序和制度的建立,一個基本功能就是約束人類本身的破壞力,約束人對其他人的傷害。社會的秩序制度被打破,就相當于分子由固態解放到氣態,必然要釋放出巨大的能量。這種沒有約束的能量當然是破壞性的,社會往往因此陷入動蕩。
因此,中國歷史上的王朝更替,無一例外都伴隨著天下大亂。而歐美等民主社會,雖然也有政府因丑聞(如水門事件)而下臺等情狀,但其間政權依然穩定,整個社會秩序制度仍在運轉,社會依然平靜。因此,可以說,號稱有著超穩定社會結構的中國傳統社會,其政治結構其實是最缺乏穩定性的。
天下大亂后,雖然社會存量遭到重大破壞,社會體質性矛盾更加突出,但是矛盾所積聚的心理能量得到釋放,結構性矛盾被瓦解,社會反而趨于平穩。所謂"大亂之后,必有大治""久亂易治",就是這個道理。
可見,社會矛盾所聚集的心理能量是誘發危機的主導因素。因此,人心向背歷來就被作為衡量政權危機程度的首要指標。"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從這個意義上說,在傳統社會內,強調"穩定壓倒一切"并非沒有道理。雖然歷代圣賢都有教誡:應付危機,疏勝于堵。但由于制度的缺陷,面對王朝末期日益迫近的危機,從來也沒有人能從圣賢那里找到有效的疏通矛盾之法。
因此,政權危機是非民主社會獨有的危機,也是它擺脫不去的最致命的根本性危機。一方面,政權因為應對和壓抑矛盾,吸附了社會長期積累的種種矛盾和危機因素,并通過這種吸附的聚焦作用和壓縮作用,將危機的能量顯著放大,而政權本身在危機爆發時也首當其沖;另一方面,對于民選政府,人民尚能容忍其部分失誤--畢竟是自己親手選出來的;人非圣賢,事有多端,難免有所失誤;實在不行,下次不讓他再上來就是了--對于非民選政府,正確則成為必須,成為政權正當性合理性的必要背書,政權背負著自我證明的巨大責任和壓力。這就是今日中國社會普遍感受到危機在迫近的首要原因。
政權危機的爆發,有兩個社會臨界點。第一是社會矛盾的積累,使相當部分人生存條件惡化;活不下去了,于是揭竿而起。這種臨界情況多發生在傳統社會自我封閉時朝,首動者往往是社會低層,如陳勝吳廣是也。第二個臨界點是由于矛盾的積累,社會百病叢生;政府面對巨大的內外危險,無力應對,處置無方;社會普遍對政權喪失信心,不再抱有指望,于是轉而自救,寄希望于政權更替。這種情況多半有外來危機的引發,首動者往往是社會精英,如孫中山是也。
不同于民主社會普選制下的公民自愿同意公開授權的法定方式,傳統社會的政權取得常常是由武力較量來決定的。但武力的較量,其中可能也包含著人心的向背,也意味著某種變相的民眾授權;因此,不可簡單地一概視之為不正當不合法。問題是這種授權是一次性的,其合理性正當性會隨著時間的推移和矛盾的滋生積累而發生變化。傳統政權形式缺乏一種自動定期地接受人民再次選擇的規范機制;實際上,不管社會危機是如何的迫切深重,政權本身是如何的臃腫腐爛,這種政權一般始終都會堅持自己自我延續的本能。這大概就是政權危機必然以沖突性破壞性形式爆發的關鍵,這也是我們今天的政治改革最終必然要面對的最根本性問題:人物有生死,世事有古今,不管再怎么擴大執政基礎,提高執政能力,政權總會有走到頭的那一天;這正如一個人不管再怎么營養鍛練,總免不了臨終一死;如果不能解決好政權怎么平穩更替的問題,人民就免不了要一次次的遭受危機折騰,社會就走不出治亂因循的怪圈,歷史就不能正常積累起進步。對于今天的中國而言,其它方法都只是治標,此處下藥才是治本。
如果說,政權危機聚集和加速各種社會危機的爆發是一切傳統人治社會的固有特征,那么幾千年的大國意識,100多年的對外屈辱史,今天被排擠在國際主流秩序之外落后于世界先進水平的現實,則是我們對外來競爭和壓力極其敏感,危機意識極其強烈的又一根源。這種危機意識滋生出的社會心理能量,如果沒有合適的渲泄渠道,最終會指向現有政權;它可能會推動政權危機加快奔向自己的第二個臨界點。這就是民族主義話語權對于傳統政權總是一件必備工具的奧秘所在。
如果說上面兩點(政權危機和外來危機)說明了百年中國的獨有困境,那么今天的中國還應該再加上一條:以改革為旗幟的社會轉型,是一場社會結構利益的大調整。其間社會變化節奏加快,人們本來就面臨心理適應的難題,積累了相當的負面心理情緒;而且,轉型過程中的所得所失,隨著改革的進程而各有不同。當改革進入攻堅期(現在就是),相當部分人的切身利益可能會暫時受到損害;而歷史和心理的慣性,又會把這種損害所造成的負面心理放大加強。因此,民眾的反應將極其強烈,并聚集起強大的社會心理能量;如果沒有合適的渲泄渠道,這種能量最終也會指向政權,并推動政權危機駛向它的第二個臨界點。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出,反腐懲貪,也是傳統政府的一大必備工具。
如果在社會轉型期間,有部分人連基本生存權利都難以得到保障,社會矛盾所積累的心理能量就有可能聚集起來,將政權危機推向它的第一個臨界點。此時,政府將不得不優先考慮社會最底層的生活保障問題,社會保障體制的構建也就成為必須,此時即使可能因此而拖累改革和發展,政府也在所不惜。因此,說危機是改革的副產品,"不改是等死,改革是找死",并非完全沒有道理。
三大獨有的危機(政權危機外來危機變革危機),與社會本身的矛盾交纏疊加在一起,共同構成了中國目前的險境。民眾的危機感其來有自,可以設想:如果我們沒有政權危機,縱然經濟落后一些,發展緩慢一些,社會也不可能發生顛覆;如果沒有外來壓力,人民縱然過得差一些,國力縱然弱一些,迭經動亂,也不會有亡國滅種之虞;如果不搞改革,人民縱然更窮更苦更沒有尊嚴自由,但如果從來就是如此,現狀即是如此,人人都是如此,不滿和抱怨,也不一定會有今天這么集中和強烈。人口資源環境經濟金融生活狀態,等等,固然都有問題,固然都潛伏危機;但最迫切的危險,還是來自上述三個方面;最核心的危機,是政權危機。
前述種種潛在危機,都有可能通過改革和發展來解決;但如果不能闖過政權這一難關,就一切都是白搭。要化解政權危機,舍民主憲政外,似乎現在還別無良方;其它的方子都只是緩解癥狀,不斷根。中國如果遲早都要走民主憲政之路,就應該盡早準備,未雨綢繆。
有人擔心以中國社會巨大的結構慣性,會不會死活不肯搞民主?這種擔心是多余的。民主之于中國,不是會不會肯不肯的問題,而是要不要能不能的問題。
中國要不要搞民主憲政,就要問民主憲政能夠為我們帶來什么。民主憲政于今之所以成為必須,不是因為它是什么普世價值(所謂普世價值,也并沒有多少現實說服力:歷史常常會迂回而行);也不是因為它真的就能"確保公民個人對國家權力的有效控制"(這顯然有些夸大其詞。它縱或能起一些作用,也需要多種條件的配合);更不是因為它就是治理國家的最佳模式(即使它是,在特定的現實條件下,這也并不足以構成我們就要向它轉軌的充分理由--因為社會轉型需要支付巨大的成本,"利不十,不變法;功不百,不易器")。我們需要它,是因為它確實能夠使社會擺脫政權危機的困擾,能夠解決統治權的正當性合理性問題(合法性不是問題。從來是先有政權后有法,制度不同法也不同)。從政權的角度而言,如果現行的政治模式仍能運行下去,仍可以維持大局,向民主憲政的轉型就暫無必要;如果危機加深了,這一套運轉不靈了,國將不國了;為避免政權與社會在危機爆發下同歸于盡,自然要求法變通--在可供選擇的成法之中,以普選制為核心的民主憲政自然會成為首選。
"能不能"順利轉型,才是問題的關鍵。事到臨頭,往往就來不及了:新的社會秩序制度體系價值體系,要憑空創造出來;舊的保守勢力,不愿意放棄既得利益;社會轉型可能會釋放出矛盾積蓄的破壞性能量,引發潛在危機。新的制度秩序能否成功嫁接在舊的環境土壤上,確實不容樂觀。
為此,政府應該具有足夠的遠見和膽魄,從現在開始就逐步開放一些公共領域,使民間力量獲得必要的自我生長發育的空間;社會上的有識有志之士,也應該及早行動起來,為未來作好準備。在這方面,張祖樺先生有個"新三民主義"(培育公民社會,啟蒙公民意識,積累民主實踐),講得很好,可作為參考。
至于改革所可能引發的并發性社會危機,確實沒有萬全之策可以應對。行路擺渡三分險,只有集合各方力量,努力將風險降至最低。社會轉型最終能否平穩著陸,還要看中國的運氣是否足夠:歷史會不會提供一個各種因緣具備,適合于解決問題的天賜良機;以及我們能不能發現和把握好這樣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