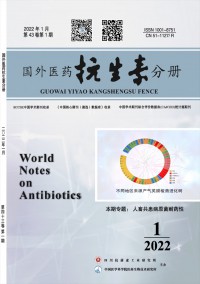國外情境修辭策略模式探究
前言:本站為你精心整理了國外情境修辭策略模式探究范文,希望能為你的創作提供參考價值,我們的客服老師可以幫助你提供個性化的參考范文,歡迎咨詢。

修辭源于演講,依賴說服性的話語策略“為沒有條理的話語提供了一個軌道”,通過互為主體性的合法化創造真理并獲得認知。而人們用以訴諸的修辭資源體現并受制于某一特定的價值取向。人類對于修辭的認知過程,同時也是“演講藝術”的演進與變遷。在柏拉圖看來,修辭與辯證是對立的,其在訴諸真理的主觀意志上存在著道德性的刻意粉飾。盡管修辭曾一度被邊緣化,但修辭學的提出標志著西方修辭學理論體系的逐步形成。亞里士多德認為,“修辭學是與辯證學相似又相對的學科”,“造成‘詭辯者’的不是他的能力,而是他的意圖”,因此其道德性取決于修辭者的說服動機。隨著修辭學的研究從語言文本延伸至社會行為,修辭的情境考量進入學者的視野,“受眾與情境適應”逐漸成為修辭者所關心的問題。LloydBitzer提出了靜態的“情境性修辭”觀點,而RichardE.Vatz認為“情境是修辭性的,而不是修辭是情境性的”。肯尼斯•伯克進一步揭示了人們構建情境修辭的動機與策略,同時將修辭重點由說服引向認同。可見,這種互動是一種以受眾為中心的受眾導向型修辭活動,演講的修辭特陛集中體現在演講者、受眾間相互制約的動態權力互動關系上,而權力的分配與遷移涉及受眾規模、群體認同特征及利益相關度等因素。根據Perelman“普世受眾”的觀點,演講者會虛構一種旨在暗示受眾被利益蒙蔽的“普世價值”,以迫使受眾認同。國內學者游梓翔提出“SPA”理論,認為演講者、演講題旨和受眾構成一個封閉式三角形,三角形面積越小,演講者要在特定受眾身上完成的特定題旨的難度也將越低。該觀點較好地分析了演講三要素的這種互動關系,但側重于對現象和結果的描述。在國內外文獻中,此類研究較少,而現有研究往往對驅動這種互動關系的內在機制缺乏系統解釋,對于不同受眾群體的反應未進行細分,對演講者如何通過控制修辭以控制權力沒有系統說明。另一方面,根據傳播學理論,受眾具有規模性、分散性和異質性等特點,其對信息的接受具有選擇性,進而可以分為積極選擇型和隨意旁觀型。傳播者對受眾的影響分為信息、情感、態度和行為四個階段。隨著傳播群體的擴大,傳播內容的針對性和具體性下降,反饋的質量和數量下降,傳播效果由個人傳播的最佳狀態逐漸發展為群體和大眾傳播的“適度效果”,因此一次具體的傳播活動對某一個接受者而言效果是有限的。根據H拉斯維爾的5W理論,傳播過程依次由誰、說了什么、通過什么渠道、向誰說、有什么效果五個基本要素構成,傳播者應分別進行控制和分析。對此,演講修辭的五藝和三訴諸可以在這種說服性的傳播過程中起到很好的作用。公共演說正是基于以上模式實現其說服效果的。CynthiaG.Emrich研究發現,美國總統的演說過程可以歸納為引起注意、增進理解、情感共鳴、回憶與詳述四個層次,而形象修辭較概念修辭更有利于塑造總統的偉人形象和領導者魅力,增強說服效果。可見,傳播理論較好地闡釋了信息傳遞過程中出現的問題,并較為嚴謹地界定了受眾范圍及其對傳播效果的影響。然而,僅從信息角度揭示公共傳播往往局限于傳媒領域,對公共演講這一特定情境下的特殊功能性表達以及存在的諸多修辭問題研究不足。本研究試圖通過“演講者—受眾”情境修辭模型的建構更好地解決以上問題。本研究將公共演講的不同受眾群體及其反應進行了細分,并對演講者應如何通過控制修辭以控制權力進行了系統說明。同時,本研究對具有典型意義的美國總統演講的說服力進行了量化分析,充分驗證了“演講者—受眾”情境修辭模型的實際效果。
二、“演講者~受眾”情境修辭模型的提出
本研究根據修辭學、傳播學及管理學等相關理論,對公共演講的情境修辭策略模型進行了分析,提出了“演講者—受眾”情境修辭模型(見圖1)。該模型旨在啟發和指導演講者在有限的理性和感性修辭元素約束下,以目標受眾為中心謀劃演講,合理配置并有效使用兩種修辭元素,實現演講效果的最大化。演講者向受眾傳播信息。對于演講者而言,其使用語言進行傳播的效果受到概念修辭和形象修辭的雙重約束,演講者必須同時不同程度地使用兩種修辭方式;對于受眾而言,其對信息接受的效果受到題旨相關程度和受眾規模的雙重約束。題旨與受眾相關度由弱變強,受眾規模由寬眾變為窄眾,從而構成了四種不同組合下的演講情境,分別為:情境I(熱烈):強題旨相關性窄眾、高概念一高形情境Ⅱ(追隨):強題旨相關性寬眾、低概念一高形象修辭情境m(猶豫):弱題旨相關性寬眾、低概念—低形象修辭情境IV(冷漠):弱題旨相關性窄眾、高概念—低形象修辭對于演講者發出的“概念一形象”修辭組合,受眾隨著規模的不斷縮小,對概念修辭的理解會整體表現出由弱到強的趨勢,同時隨著題旨相關度的增強會整體表現出對形象修辭由高到低的需求趨勢。由此,強相關性窄眾表現出對“高概念一高形象”修辭組合的偏好,強相關性寬眾表現出對“低概念—高形象”修辭組合的偏好,弱相關性寬眾表現出對“低概念—低形象”修辭組合的偏好,弱相關性窄眾表現出對“高概念—低形象”修辭組合的偏好。演講者在修辭時需要考慮受眾在不同情境下的偏好,并盡量將情境修辭區問鎖定在I、Ⅱ兩個范圍內,以增強說服效果。由于修辭情境是一種動態互動過程,受眾并不必然靜態分布于這四種情境下,而是存在相互影響并發生動態遷移。受眾I表現為理性熱情,受眾II表現為感性熱情并可能因受眾I影響而發生遷移,受眾Ⅲ表現為無所謂態度并可能因題旨相關性的增強而發生遷移,受眾Ⅳ表現為理性冷漠并可能因受眾ⅡI影響而發生遷移。演講者在修辭時可以通過受眾間的互動關系增強演講的說服效果,同時應盡量減少因受眾逆向流動造成說服效果的減弱。
三、美國總統演說說服力的回歸分析
本研究基于C—SPAN的美國總統排名數據,以說服力為參照系,通過相關性分析和回歸分析兩種路徑考察其他利益要素和受眾范圍對說服效果的影響。通過應用SPSS軟件對以上排名相關性進行回歸分析發現,專家組與大眾組的評價結果相近,但在對分項評價過程中大眾組排名相關性較強,而專家組差異明顯,這反映出大眾在評價過程中感性因素較為突出,而專家組則表現出較高的理性。通過對說服力前十進行分析發現,在大眾組看來,與說服力相關性(如圖)較強的指標依次為履職情況(1.000)、經濟管理力(0.952)、危機領導力(0.892)、愿景(O.832)、與國會關系(0.832),而在專家組看來,相關系數最高的為說服力與愿景,僅為0.645。此外,愿景和與國會關系在大眾看來具有強相關性(1.000),這同時表明影響訴諸效果的其他某些利益要素間并非相互獨立,相反其相關度高低會最終影響訴諸力的強弱。有鑒于專家組各指標與說服力相關度較弱,因此本研究著重考慮對大眾組進行回歸分析以證實寬眾群體與說服效果的聯系規律,并選取大眾組中最具研究價值的相關系數0.900以上的指標進行回歸分析,結果如下。三個指標回歸式常數均不明顯,回歸式常數和回歸系數95%置信區間均不大,回歸系數均明顯。這說明該三項指標與說服力具有很強的線性相關性。進行相關性和回歸分析的意義在于,從受眾視角分析不同的演講題旨分別在多大程度上影響演講者的說服力,而演講者應當如何合理分配不同話題的比例以最大程度地增強說服力。研究發現,專家組對各指標對說服力的影響并不敏感,表現出較高的理性選擇,因此需要就具體話題引入較多的概念修辭以增強對專家組的說服力。從各指標均表現出與說服力的高相關性看出,大眾具有較高的感性認知度,以上各項對說服力的提高均有意義,因此需要演講者更多地使用形象修辭以增強對大眾的說服力,同時要注意話題的分布,對強相關度話題應有更多的側重。例如,總統任期履職情況與說服力具有強相關陛,意味著演講者應在形象修辭過程中強調承諾的執行力度與執行途徑,以創造其“人格可信性”(克里斯托弗•胡德2004),這一點在歷屆總統就職演說中均具有決定意義;危機領導力和經濟管理能力具有強相關性的意義在于,總統就職演說往往創造一種“情結氣氛”,通過塑造危機以結束爭論,有利于公共管理人員在描繪愿景的同時塑造領導者魅力;愿景和與國會關系具有強相關性(1.000)的意義在于,在演講中倡導或滲透此類話題將會加倍說服效果。在題旨相關性方面,著重引用強相關性話題會造成核心受眾的強關注度,進而出現可能的集聚效應以吸引寬泛受眾的注意力。另一方面,克里斯托弗•胡德(2004:187)認為,公共管理中“公認”觀念的變遷是通過一種流行和勸服過程實現的,為使認證顯得可信而又避免使用“硬數據”或邏輯認證,通常可運用隱喻、提喻、轉喻、諷喻四種比喻性的修辭方式。公共管理中雄辯家的技巧在于他們善于選擇與題旨及受眾相適合的隱喻或有效的反喻。根據CynthiaG.Emrieh的研究,形象修辭對塑造領導者魅力平均貢獻值為15%,而對塑造偉人形象的平均貢獻值為22%。“演講者一受眾”情境對這一觀點進行了有利的支撐,即這種側重運用形象修辭打動受眾以產生共鳴的策略,在美國總統就職演說中大量運用。通過“演講者—受眾”情境模式并結合統計回歸方法,從規范和實證兩方面對美國歷屆總統就職演說進行研究,不僅有助于受眾客觀理性把握演說的實質,對演說者及演說稿撰寫者亦起到指導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