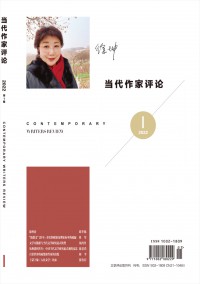遲子建丈夫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嗎?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5篇遲子建丈夫范文,相信會為您的寫作帶來幫助,發現更多的寫作思路和靈感。
遲子建丈夫范文第1篇
偶然相識,
頂著外界非議牽手“富婆”
遲重瑞1952年出生于北京的一個五代京劇世家,但因他1.82米的身高,最終卻沒能走上京劇之路。從上海戲劇學院畢業后,他來到中國電視劇制作中心,成為一名職業演員。
1988年,《西游記》在全國首播,引起了很大的轟動。遲重瑞飾演的唐僧得到了廣大觀眾的一致認可,師徒四人一時間成為最受歡迎的明星,所到之處,備受關注。隨后,遲重瑞的愛情也悄然而至。
陳麗華是個票友,酷愛京劇,1988年冬的一天,她來到中國京劇院唱戲,遇見了遲重瑞。當時,電視劇《西游記》紅透全國,遲重瑞這個名字幾乎家喻戶曉。陳麗華和遲重瑞客串過幾出京戲,感覺這個小伙子為人很誠懇,是個值得交往的朋友,不過沒往別的地方想。京劇院一個朋友見兩人都單身,便毛遂自薦當月下老人。陳麗華一聽連連擺手:“不行,不行,人家比我小11歲呢。”朋友不死心,又去“磨”遲重瑞,了解了陳麗華的家世和經歷后,他大吃一驚,覺得這簡直就是個奇女子!
原來,陳麗華在北京頤和園出生、長大,滿族后裔、正黃旗世家。用現在的話說,就是位“格格”。然而幼年因家境破敗十分貧寒,讀到高中便被迫輟學。為生計所迫,陳麗華做起了家具修理生意,由于她頗具生意頭腦、待人熱忱講信用,生意紅紅火火,很快辦起了自己的家具廠。1981年初,陳麗華從北京來到香港,通過實力人物的幫助,從事房地產投資。陳麗華在香港的第一桶金是在比華利買了12棟別墅,不久高價賣出,獲利頗豐。她在香港完成原始積累后,便成立了富華國際集團,自任董事長。接著又向港島外拓展投資。
兩人在一起的時候,遲重瑞特別怕別人發現,總是提心吊膽。陳麗華問他為什么要這樣。遲重瑞喃喃半天,說出了心里話:“咱倆的事,劇院里已經風傳開了,有人說我傍大款,有人說我吃軟食兒,難聽極了。”
陳麗華心里很難過,過了沒多久,陳麗華提出結婚,她認為:只有登記結婚了,才能使那些謠言不攻自破。兩人去南美洲蜜月旅行回來,陳麗華把最好的朋友都請到新家聚會。酒酣耳熱之際,陳麗華的一個女友要求大家安靜一下:“我在書房里發現了一封信,在這喜慶的時刻,我決定把這封信公之于眾,即使因此得罪了麗華,也在所不惜。”在這封信里,陳麗華向遲重瑞表達了自己的愛慕之情,言真意切,比瓊瑤的小說還純情。信還沒念完,大家都樂得笑出了眼淚。
唯一感到莫名奇妙的是遲重瑞,陳麗華什么時候給他寫過這樣一封“肉麻”的情書呀?陳麗華悄悄掐了一下他的手,示意他別作聲。遲重瑞恍然大悟:原來,這是愛妻導演的一出戲呀。眾人離開后,遲重瑞眼含淚花說:“其實,你本可以不必這樣做的。只要我們相愛,別人說什么,又有啥關系呢?我們不必多作解釋。”陳麗華幸福地依偎在丈夫胸前,低聲笑著說:“這叫舍卒保車嘛。”
投其所好,
太太讓他事業愛好合二為一
當時,陳麗華女士是中國女首富,擁有上億元資產,她比遲重瑞大11歲,而且離過婚,身邊帶著三個孩子(一個兒子兩個女兒)。他們的結合立刻引起了人們的關注,很多人質疑這段婚姻的感情含金量。面對媒體的質疑和猜測,遲重瑞說:“我們不用表白,時間會證明一切。”選擇了事業女強人陳麗華,也就意味著選擇了付出。
婚后不久,兩人遷居香港。遲重瑞悄然退出娛樂圈,開始新的生活。陳麗華深愛丈夫,給他買名牌西裝,買10克拉的鉆戒,給他建大游泳池……遲重瑞總是推辭。陳麗華不理解:“我只是想表達對你的愛。我們結婚了,我人都是你的了,錢還分什么你我?”
1998年,楊潔導演籌拍《新西游記》,希望遲重瑞重出江湖。遲重瑞十分振奮,可陳麗華十分矛盾:丈夫已是快50歲的人了,去云南深山老林一拍就是一年,身體能吃得消么?再說,夫妻兩人終日相守,感情深厚,他這一走就得一年……堅強的陳麗華流下了淚水。遲重瑞說:“如果你不想讓我去,我就不去了吧。”陳麗華破涕為笑說:“我不是不想讓你去,我是替你高興。”
很多人不了解的是,遲重瑞有一副天生的好嗓子,《新西游記》中的插曲《看我躍馬揚鞭》《晴空月兒明》都是他演唱的。這期間,遲重瑞在云南劇組里,吃的是方便面和盒飯,坐的是小面包車……這一切,他都克服了,唯一讓他掛念的是愛妻。兩人天天通電話,連劇組里年輕人都開他的玩笑:“談得這么熱乎?是嫂子呢,還是小情人?”遲重瑞鄭重地回答:“是你嫂子,也是小情人。”
隨著中國房地產業的起飛,陳麗華的事業如日中天。可《新西游記》帶給遲重瑞的成功感,卻隨著時間的流逝而消失了。遲重瑞終于感到,自己該退出影視舞臺了。這令他感到沮喪,自己什么也做不了,豈不成了沒用的人?
陳麗華知道,夫妻之間如果無法找到共同話題,是很容易出問題的。她經常邀請丈夫一起去參加商業談判和項目決策會,可遲重瑞對生意就是找不到感覺。他對妻子說:“你的心意我領了,可我勸你別浪費腦細胞了,我不是做生意的料。”
陳麗華天生有一種不服輸的性格,總希望在沒有辦法中找出辦法。有一天,陳麗華領丈夫回北京自己的老家,遲重瑞無意中看見了一件古檀木刻件,高興地拿在手里,把玩不已。他告訴陳麗華,中國古代有“寸檀千金”之說,檀木樹質極堅硬,一百年才長一寸,歷來是宮廷里的寵物。這種紫檀更加名貴,由于濫砍濫伐,幾乎絕種,留存世上的檀木刻件,件件都是稀世珍寶。
看到丈夫講起檀木來眉飛色舞,陳麗華的心猛然一震:既然檀木如此珍貴,我能否往這方面發展?這樣不就可以和丈夫“志同道合”了嗎?他們馬上去了北京一些文物商店,果然,檀木作品非常稀少。從此,遲重瑞開始收集古家具,后來自己又采購紫檀做家具。時間不長,他擁有的紫檀家具、器物越來越多。憑著多年來的經商經驗,陳麗華斷定,檀木市場有巨大商機。
這時候她就想,何不蓋一個博物館,把這些紫檀家具陳列在里邊,向世人展示?2002年,陳麗華投下2億元巨資,在北京北四環邊兒建了世界上唯一一座檀木博物館——中國檀木博物館。遲重瑞對這項符合他藝術氣質的工作表現出了極大的興趣,從博物館設計圖紙的審定,館內藏品的分類原則,到藏品的收購,檀木原料的采購等等,他都是親自決定。多年來習慣了妻子拍板決定,如今一下子改由自己拍板,這種感覺真美妙!陳麗華知道自己在這方面是外行,她無比信任丈夫,丈夫的話,她言聽計從。這樣的生活,給夫妻倆帶來了全新的感覺,遲重瑞一下子變得格外振作,仿佛換了一個人。
一起變老,
老妻少夫演繹“最浪漫的事”
從原來的“遲老師”到現在的“遲總”,遲重瑞認為自己算不上商人:“真正商業上的事務還得靠我的夫人,都是由陳麗華和她的兒子趙勇去做的。做紫檀家具,經營紫檀博物館,我基本還是沒有離開藝術的。博物館并不賺錢的,每天的電費、清理費、服務人員的開支等等都需要很大的開銷,好在我們的企業大,有足夠的資金來養這個私人博物館。”
遲重瑞鐘愛紫檀已經到了虔誠的地步:“紫檀還是高級藥材呢。在紫檀旁邊坐著,就跟喝了咖啡似的特別有精神。特別累時在紫檀邊走一圈,什么頭疼啊煩惱憂愁全都沒有了。紫檀能通血,黃花梨能降壓。”他辦公的地點是一座十幾層高的大樓,整棟樓裝修考究,有媒體用“宏偉壯觀”形容。辦公樓叫做“麗華閣”。“麗華閣”內部設計也十分莊嚴肅穆和豪華奢侈,仿佛一座古代宮殿。
遲子建丈夫范文第2篇
【關鍵詞】孔雀東南飛;問題分析
【中圖分類號】G633 【文獻標識碼】A
一、劉蘭芝忍辱負重是否可以維系自己的婚姻
有人認為,若劉蘭芝對婆婆的小折磨能夠隱忍不言,就不致引起丈夫對婆婆的不滿,因而也不會引發婆婆與丈夫的激烈沖突,不致使自己被婆婆所遣。此論似是而非。
蘭芝成婚二三年來,與丈夫“相見常日稀”,但是蘭芝“守節情不移”,而且“雞鳴入機織,夜夜不得息”。可以說肩挑著家庭重擔的蘭芝是一個優秀的妻子,一個稱職的兒媳。那為什么焦仲卿的母親還要兒子(將兒媳)“便可速遣去,遣去慎莫留”呢?焦母自己的說法是“此婦無禮節,舉動自專由”;劉蘭芝的理解是“三日斷五匹,大人故嫌遲。非為織作遲,君家婦難為”,就是說,婆婆的指責只是一種借口而已,再能干的媳婦,也難在焦家立足。
劉蘭芝的感覺是對的――婆婆對兒子直言不諱地說:“吾已久懷忿,汝豈得自由?”“東家有賢女……阿母為汝求。”看來,焦母對兒媳的不滿已經積壓久矣,達到了必欲休之的地步,她甚至將下任的兒媳都物色好了。至于人家允不允婚,婚后是否稱他之意,那是另一回事了。可以確定的是焦母休媳的決心早已下定,兒子前來為愛妻道委屈,正好引燃了她的火藥桶而已。
因此可以說,焦母休媳之心早已有之,翻臉只是早晚間事,蘭芝再忍辱負重也于事無補。從這個角度說,焦劉二人婚姻悲劇的首惡就是焦仲卿之母了,她的專橫,她的挑剔,她的不容,毀壞了一樁好婚姻,拆散了一對恩愛夫妻。至于焦母為什么視兒媳為眼中刺,必欲去之而后快,后文再做論述。
二、焦母為什么不喜歡劉蘭芝
焦仲卿的母親對劉蘭芝的態度可謂“深惡痛絕”,面對兒子“今若遣此婦,終老不復取!”的激烈反抗,面對兒子“兒今日冥冥,令母在后單”的絕命警告,她一再無動于衷,一點也不肯給兒子(實際是不肯給兒媳)讓步,以至于釀成悲劇。我們不禁要問:何以至此?
首先,可以排除焦劉二人因自由戀愛成婚而引發焦母不滿這一條,因為詩中沒有絲毫的蛛絲馬跡。
按照焦母的說法:“此婦無禮節,舉動自專由”――這也許是存在的,畢竟劉蘭芝是十七八歲的青年(現代人眼中這個年齡段還是“孩子”),言語、行動難免有不當之處。但是,被扣上“無禮節”的帽子,性質可就嚴重了,漢朝“七出”中的首條就是“不順父母”,即對不順父母的婦人,男方可以無條件離婚。其實,“無禮節”的真正秘密可能就是“舉動自專由”。一者,家中除了焦仲卿年幼的妹妹之外,只有一個中年失偶的婆婆和一個長年“留空房”的新媳婦,兩人在一起有多少話可說呢?交流之少是確定的了。郁悶就是家庭的氣氛主調了。蘭芝只能埋頭干活以排解苦悶,婆婆就要專享婆婆之威福了。他要的是兒媳的低眉順眼、母長母短的問候與請示。問題是劉蘭芝非常聰明、極為能干,這種人一般長于做事而拙于“做人”,她會果斷干練的干好自己的事,可能不會花費心思去討婆婆的歡心,這就被婆婆視為“舉動自專由”了。但她肯定不是一個“無禮節”的人,你看她在遭遣離家之際,辭別婆婆時自謙地說:“生小出野里,本自無教訓”,又關切地說:“今日還家去,念母勞家里。”說明蘭芝是知書達理之人。與蘭芝的聰慧、明理相比,婆婆就相形見絀了,婆婆能不因而心生嫉妒嗎?
正是因為蘭芝的美麗、明理、能干,徹底地俘虜了焦仲卿的心,以至于說出“兒已薄祿相,幸復得此婦”的話,此話在焦母看來是沒有志氣的話,這種兒女情長的表現為封建社會的家長普遍不滿(如陸游的愛妻唐婉兒是從小青梅竹馬的表妹,是雙方家長滿意的婚姻,只因為夫妻倆過于恩愛,陸游母親怕耽誤了兒子的前程,竟毅然驅遣了親侄女),更何況焦仲卿言下之意是滿足于一個好媳婦,竟無心上進了。而焦母認為“兒是大家子,仕宦于臺閣”,雖為小吏,但是還正年輕,前途未可限量啊。兒子卻流露出無心上進之意,豈不更令母親惱火,說不定她因此而把蘭芝視為影響兒子上進的“禍根”。
如此說來,劉蘭芝被婆婆深惡,竟然不是因為不肖,而是因為優秀。
對封建社會的已婚中國女人來說,靠山有三。一是丈夫,二是娘家,三是兒女。劉蘭芝固然有愛她的丈夫,但他不是強悍的母親的對手,不能盡到保護妻子之責;而娘家呢,母親只有“大悲催”,徒自悲憤而已,兄長呢,也沒有出頭為妹妹做主(主倒是做了,不過做的是逼妹再嫁)――蘭芝還能指靠什么呢?兒女嗎?說到這,倒是引出了一個新的猜測,劉蘭芝結婚兩三年了,仍未生育,這也可能是婆婆不待見她的又一重要原因了。如果她生有一男半女,想必婆婆也不會像這樣逼人太甚吧?
遲子建丈夫范文第3篇
當然,還有一點不可否認,那就是男子漢們在生活上的“不檢點”,例如吸煙、酗酒、賭博、暴飲暴食,遠遠多于女性,也是其變得“脆弱”、需要關懷的一個重要原因。
那么,怎樣去關懷男性呢?以下幾點可供參考: 1.理解丈夫的事業心 許多男性事業心很強,成天忙于工作,甚至晚上還加班加點,挑燈夜戰。作為妻子應該給予理解,支持丈夫的事業,并幫助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以減輕他的壓力。與此同時,也要愛護丈夫的身體,合理安排好作息時間,建立科學的生活方式,使其倍感妻愛的溫馨。
2.與丈夫分擔喜和愁 男人們終日處于激烈競爭的環境中,會受到各種有形或無形的壓力,如果壓力過大或持續時間過長,則對健康十分有害。醫學研究已經發現,不良的壓力可削弱人體的免疫力,也是身心疾病之源。因此,細心的妻子應該關注丈夫的情緒變化,無論是成功帶來的過喜壓力,還是失敗造成的焦慮壓力,都要予以及時排遣,提醒他“不以物喜,不為己悲”,淡泊名利,泰然處之,把煩惱關在門外。妻子和丈夫應該多交流,相互學習,共同領略、品味人生。只有學會了駕馭自己的情緒,才能視壓力為動力,才能精神抖擻地去學習、工作和生活。
3.規勸丈夫善待生命 美國著名作家愛默生說:“健康是人生的第一財富。”當今不少男子對自己的健康很不注意,既吸煙,又喝酒,飲食不節,不愛運動,甚至尋花問柳,結果病魔纏身,后悔莫及。因此,妻子應從關懷、愛護出發,動之以情,曉之以理。
遲子建丈夫范文第4篇
屋里冷清清的,妻子李玉蓮坐在破舊的沙發上,癡癡地看著進了門的丈夫發笑。大胡看了妻子一眼,微笑著連說帶比劃地詢問了妻子上午的情況。李玉蓮嗯嗯呀呀地比劃著,意思是很好。
大胡洗了手,開始準備午餐。吃過飯休息會兒,下午再去地里轉一轉。吃過晚飯他便攙扶著妻子在團場轉一轉。
這樣的日子大胡已經習以為常,這也是他4年來最真實的生活寫照。大胡悉心照顧失去生活自理能力的妻子的事跡,也在團場廣為流傳。
中年有了家
1979年,19歲的胡成安從四川老家獨身來新疆謀生。他的母親和弟弟在兵團十三師紅星二場打工,胡成安投奔親人而來。
胡成安個子不高,憨厚老實,一直靠打零工為生,收入不高。
2000年,大胡的母親撒手人寰。弟弟胡成錄成了七連的一名職工,早就有了家室。母親在世時還一直操心著大胡的婚事,自從母親去世后,大胡對自己的婚事更沒了信心。從此過著一人吃飽,全家不餓的生活。
2004年,七連退休職工馬文俊熱心地給胡成安牽了紅線。老人將連隊職工李玉蓮介紹給了胡成安。
李玉蓮是土生土長的兵團二代,丈夫因病去世,留下一個兒子。
2004年1月2日,44歲的胡成安和比自己小7歲的李玉蓮喜結連理。嘗遍了人間酸甜苦辣的大胡,終于有了一個家。盡管這個家并不富裕,但大胡知足了。因為有了一個知冷知熱的妻子,還有一個14歲的兒子。
悲喜交加時
婚后的生活甜蜜而溫馨。大胡在連隊疼老婆是出了名的。只要他在家,一般都是他做飯。地里的活,大胡一個人包了下來。回到家,要是看到妻子拎個重東西,大胡會跑步過去搶過來,說啥也不讓妻子累著。
正當他們沉浸在家的溫馨中的時候,厄運向他們悄悄地襲來。
2009年7月的一天,大胡正在地里勞動,大舅哥李建明突然打電話,說李玉蓮病了,讓他趕快回來。
經過三天的搶救,李玉蓮轉危為安。醫生診斷是高血壓引起的腦梗。本來家里就不富裕,李玉蓮這一病,更是雪上加霜。就在李玉蓮入院不久,李玉蓮的兒子遲宏斌收到了武漢科技大學交通管理系的錄取通知書。
一面是妻子看病要用錢,另一面是兒子又馬上要上大學,更需要用錢,可錢從那里來呢?
大胡的棉花每年收入只有一二萬元,家里沒多少積蓄。面對妻子看病和兒子上大學,大胡一夜愁白了頭發。大胡的二舅哥李建新家里條件比較好,他借給大胡二萬元錢應急。
大胡精打細算,安排好兒子上學和妻子看病的事。住院期間,為了讓妻子早日康復,大胡想方設法給妻子調劑好營養,而自己每天吃個馕餅充饑。
住院期間,大胡的39畝棉花地就交給兩個舅哥管理,他全身心地照顧妻子。醫院對李玉蓮作了全面的檢查,李玉蓮還患有脂肪肝和癲癇。出院后,李玉蓮遺留下了后遺癥,偏癱失語,失去了生活自理能力。
一個月后,遲宏斌順利地走入了理想的學府。李玉蓮回家調養。從這以后,照顧李玉蓮的重任就落在了大胡身上。
敢于擔當
面對命運的一次次戲弄,大胡沒有怨天尤人,而是默默無聞地承擔了下來。
李玉蓮回來后,完全失去了生活自理能力。吃飯得人喂,大小便也不能自理。大胡把妻子當成自己的孩子一樣精心伺候。每天下地前,他把妻子的飯菜做好放在跟前。回到家里,他顧不上吃飯,先要看一下妻子有沒有尿床,需不需要更換衣服。剛開始收拾妻子拉在床上的屎尿時,大胡屏著呼吸惡心地快要吐了。后來他也慢慢地習慣了。
為了調理李玉蓮的心情,也為了不讓妻子的肌肉萎縮,大胡找來兩根粗鋼管,在大舅哥的幫助下又栽了四根木棍,把鋼管放在棍子上,擔成了雙杠。只要有時間,大胡就攙扶著妻子出來在雙杠前練習走路。
四年來,由于照顧妻子,供兒子上學,大胡瘦了一圈。頭發也白了,臉上的皺紋也多了。他也沒有給自己添置過一件像樣的衣服,家里也沒有一件值錢的家具。妻子也從來沒有開口說過一句話,沒有叫過他一聲老公,但每天看著妻子的笑容,再多的苦與累,大胡都覺得值了。
夏去秋來,四年光陰過去了。如今,遲宏斌已經大學畢業了,現在外地實習。李玉蓮的病情也有所好運,基本可以獨立行走。大胡也還完了借二舅哥的錢,心里也舒坦了一些。
遲子建丈夫范文第5篇
但是,我終于還是讀了這部《額爾古納河右岸》。最初的原因是它獲得了“茅盾文學獎”,授獎辭中說它,“具有史詩般的品格和文化人類學的思想厚度”。當然,并不是獲獎的書就值得購買,對另外三本書我就毫無興趣——因為他們達不到我的閱讀要求。
我從一個陽光照耀的初春的上午開始閱讀此書,幾乎是手不釋卷,在第二天讀完了“清晨”和“正午”兩個部分。我得說,這是一部了不起的作品,在閱讀中我有了基于文學本身的久違的沉浸。即使作為一個挑剔的讀者,也不得不由衷發出贊嘆。
作品以鄂溫克最后一個酋長女人的口吻,敘述一個民族的生存、堅守和文化變遷。“我是雨和雪的老熟人了,我有九十歲了。雨雪看老了我,我也把它們給看老了……”這是它的第一個句子。這些比喻的、完成式的、嘆息著的句子,有一種來自命運本身的蒼茫意味,簡約、直接,使憂傷與詩意洋溢而出,為整部作品確定了基調。
這部作品有著強烈的“唯心”色彩,大自然中的樹木、野獸、河流、天空、星月,有著和人一樣的靈性,或者說是神性,這使它超脫出我們當下的塵世經驗,顯現出清新、原始的格調。奇怪的是,在閱讀過程中,它常常引發我類似懷鄉的憂愁——我會忽然想念已經遠逝的蔥蘢歲月、想念少年時代的田野、某個初春曾經去過的山林,想念起初戀或者傾心夜談的朋友。
有多個評論說,這部作品是一個民族的史詩性挽歌,如果以一個讀者看,這首挽歌并不單單是哪個民族的挽歌,抑或還可以說是一曲關于某種美好生活的挽歌、關于人類某種價值觀和生命方式的挽歌。人們仰望天空,沉醉河流和山林,心中敬畏神明,唱著單純的歌曲,生于“風聲”,最后又被埋葬于風中。作品中除了作為主要人物的形象之外,更為動人的是變化的白云、閃爍的星光、能望見天空的希楞柱、馴鹿、月亮、薩滿的舞蹈、樺樹與松樹、明亮的流水,它們既是人物的生活背景和依據,也同樣是書中的主角。它們共同構了這個世界美好而又脆弱、歡樂與苦難交織、幸福中滿含悲傷的生命景象。
“精神清冽,內心溫暖。”我這樣指認遲子建小說的特質,她的一系列以中國最北方為地理環境的小說,大多有著白雪墓園般的安靜,空氣寒冷,一塵不染,卻又有著靜靜燃燒的火堆般的心情。在那里,人類有著美好的品行,似乎人類與世界、自然以及宿命已經和解,因此苦難和死亡不再是可怕的和痛苦的,而僅是生命的另一內容。如今這部《額爾古納河右岸》,除了她一如既往的真摯、澄澈和溫情脈脈,我從中讀到了更多的哀傷和悲憫。我一直認為,一個作家具有寬闊深刻的悲憫情懷,才有可能走向偉大!那么這部作品是一個作家持續成長的結果?還是遲子建本人的生命歷程獲得了文學上的補償?
我曾從作家王樹增口中聽說,當年在北師大作家班同學時期,莫言和遲子建是兩位最勤奮的作家,每天就是大量讀書、寫作,據稱遲子建每天能寫一萬字。這點,我們從遲子建海量的作品中就可以想見。“天賦是靠不住的,出類拔萃需要長久不懈的努力。”另外,作家的個人經歷也會影響她的作品。大約在2002年,也就是寫作這部作品的三年前,遲子建的丈夫(漠河縣委書記)因車禍撒手人寰,一對相敬如賓、恩愛有加的情侶從此天人永隔,可以想見,那種悲傷是如何讓遲子建身心痛徹,我們并不知道在以后數年她如何從中恢復,在她的生命中又留下了怎樣的痕跡。但是我相信,《額爾古納河右岸》這部作品中,有了以前所沒有的東西,看看她對一個個死亡的描述,那里有多少沉重的的嘆息和無奈的與淚水!
作為一個小說家,遲子建從來就不以塑造人物、講故事、設計沖突和結構見長,而是以優美的語言、從容的節奏、豐富的意象取勝,她所做的不是描繪具體事物,而是傾述,從內心向世界的傾述。事物經過心靈的含蘊之后,再表達出來,那些文字就被賦予了精神意義。語言因此產生了內在的節奏和張力。品讀一下某些段落,它們幾乎可以詠唱,即使并不押韻,卻有一種明顯的音樂性。
我以為,中文之美包括了多個層面,每個字詞在它有本來意義之外,還有著獨特的形狀,獨特的色彩,獨特的聲響,甚至還有獨特的味道和觸感。從事寫作的人,如果反復推敲過一萬個以上的好句子,最好是你曾經有較長的詩歌寫作經驗,就一定會對文字的形狀、色彩、明暗、聲音和氣味有所領會。
遲子建這部作品中的語言,可能是她作品中是好的語言(我能不能說也可能是中國當代小說中最好的語言?),比喻豐富,感情充沛,色彩絢爛,節奏感極強,就像那條閃光的額爾古納河,豐盈、寬闊,伴隨著風的歌吟,在夏日山谷中湯湯流動。當然,它述說的是一個關于生命與死亡的故事,關于美與哀傷的故事,也是一個關于出現和消逝的故事。
已經寫得太長,但我還有另外的話說。
這部小說盡管優秀,卻遠非完美。
我的所有關于“好”的感想,基于本書的前兩個部分,“清晨”和“正午”。我認為“黃昏”一章的寫作水準與另外的部分有著較大的差距,它顯得駁雜、氣短,就像一個奔跑者忽然力有不逮,開始上氣不接下氣。這不能歸結于本章所要表達的時代內容,即使單從語言上看,它的節奏在許多地方已經失去了。
長篇小說的創作,是對一個作家心力和體力的雙重考驗,即使作家有很充分的準備、很充沛的激情,也需要掌握合適的進度。在后面的跋中,作者說自己兩個多月寫成了它,而在第二卷之后回了哈爾濱,依我看,就是從那里,第三卷發生了松弛和潰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