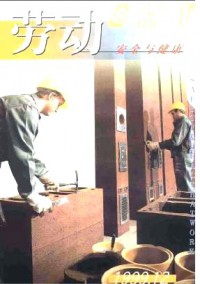論勞動合同法健全思考
前言:本站為你精心整理了論勞動合同法健全思考范文,希望能為你的創作提供參考價值,我們的客服老師可以幫助你提供個性化的參考范文,歡迎咨詢。

內容提要:立法宗旨集中地體現了一部法律的基本價值判斷準則。從《勞動合同法》立法過程中的激烈爭辯可以看出,立法宗旨問題關乎我們對勞動合同法的定位以及對其根本性質的認識。在承繼勞動法立法宗旨的基礎上,傾斜保護的社會法思路應該成為勞動合同法的基本指導思想。
作為最集中體現一部法律基本價值判斷準則的立法宗旨,它的確立關乎我們對于一部法律的性質的基本認識。《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合同法》(以下簡稱《勞動合同法》)的立法宗旨是立法過程中激烈爭辯的內容。
在《勞動合同法》起草過程中,其立法宗旨的表述四易其稿,在表述上存在著某些一致的地方,也存在著一些變化。對4次審議稿中立法宗旨的演變過程進行回顧,我們能夠清晰地看到立法者的思維軌跡。
4部稿子4次審議中,沒有變化的內容主要有:一是,一直強調保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二是,一直強調勞動關系和諧穩定。
4次審議中,發生變化的內容主要有:一是,一審稿中強調規范用人單位與勞動者訂立和履行勞動合同的行為;二審稿強調規范用人單位與勞動者訂立、履行、變更、解除和終止勞動合同的行為;三審稿和最終稿提的是完善勞動合同制度。二是,一審稿、二審稿都以《勞動法》作為立法依據;三審稿、最終定稿中都沒有再提以《勞動法》作為立法依據。三是,最終定稿與一審稿、二審稿、三審稿中有顯著變化的是增加“明確勞動合同雙方當事人的權利和義務”以與“保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相配套。
一、勞動合同法立法宗旨爭論及其質疑
在勞動合同立法過程中,關于立法宗旨,勞動法學界出現了所謂“雙保護”和“單保護”之爭。所謂“單保護”,是指“保護勞動者合法權益”;所謂“雙保護”,是指“保護勞動者和用人單位合法權益”。有人認為立法必須在“雙保護”與“單保護”之間做出非此即彼的選擇[1]。更有人認為,勞動合同立法發生了所謂從“雙保護”到“單保護”,從民法調整到社會法調整的變化[2]。
“雙保護”觀點是學者對某些人大常委會委員觀點的一種概括。例如,曾憲梓在《勞動合同法(草案)》進行第3次審議的時候,認為“勞動合同是由勞資雙方簽訂的,既應該保護勞動者的利益,也應該保護雇傭勞動者的人的利益。我們制定勞動合同法,就應該兼顧各方的利益,保護各方的權益。”倪岳峰委員也建議“在草案第一條的立法目的中將‘保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改為‘保護勞動者和用人單位的合法權益’。”[3]厲無畏在接受媒體采訪時也表示,勞動合同法一是要保護勞動者,二是要保護企業。保護了企業也就是保護了勞動者,企業的權益無法保障,勞動者的最終權益也無法保障[4]。
主張所謂“單保護”觀點的多見于勞動法學研究者,最主要的代表是王全興。他認為:任何一部法律或一個法律部門,對所調整的社會關系的各方當事人都會保護其合法權益,但在立法目的條款中有的作‘雙保護’表述,有的作‘單保護’表述。前者如《合同法》第1條中“保護合同當事人的合法權益”的規定,這意味著給雙方當事人以同等力度的保護,即平等保護;后者是將保護某方當事人合法權益在立法目的條款中作明確表述,而將保護他方當事人合法權益的精神蘊含于其他條款中,如《擔保法》第1條中“保障債權的實現”、《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1條中“保護消費者的合法權益”、《勞動法》第1條中“保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刑法》第1條和《刑事訴訟法》第1條中“懲罰犯罪,保護人民”。這只是表明偏重或傾斜保護某方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即對某方當事人的保護力度相對較大,并不意味著只保護某方當事人而不保護他方當事人。勞動法區別于民法的根本標志是,勞動法基于勞動關系中勞動者是相對弱者的假設,在保護雙方當事人合法權益的同時,偏重保護勞動者合法權益,故立法目的條款中作“單保護”表述;民法基于平等主體的假設,對當事人雙方的合法權益給予平等保護,故立法目的條款中作“雙保護”表述[5]。
涉及勞動法的宗旨,觸及了勞動法學界最敏感的神經。于是一些德高望重的前輩學者,以“義無反顧”的堅定姿態發表了支持“單保護”的觀點:“《勞動合同法》是《勞動法》范疇中的單項法,是《勞動法》法律體系的組成部分,當然其立法宗旨應與《勞動法》相一致,應當明確提出“根據《勞動法》制定本法”。在1994年頒布的《勞動法》第1條中規定:“為了保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調整勞動關系,建立和維護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勞動制度,促進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根據憲法,制定本法。”既然《勞動法》開宗明義地提出“為了保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為其立法宗旨,當然作為勞動法法律體系的《勞動合同法》義無反顧地亦應以保護勞動者合法權益作為立法宗旨。”[6]
但依筆者的看法,爭議過程中一些學者的論述有站不住腳的地方。
首先,“單保護”論者將“單保護”與“雙保護”作為立法的一項基本分類標準,這種分類欠妥。按照這些論者的觀點,任何一部法律或一個法律部門,對所調整的社會關系的各方當事人都會保護其合法權益,但在立法目的條款中有的作‘雙保護’表述,有的作‘單保護’表述。[7]然而,當代立法宗旨極其多樣,恐怕很難將所有的法律統統歸人“單保護”與“雙保護”的分類中。正是這種不恰當的分類,使論者自己陷入了邏輯混亂。按照論者的論述,《刑法》也是屬于“單保護”的。“《刑法》第1條和《刑事訴訟法》第1條中‘懲罰犯罪,保護人民’,這只是表明偏重或傾斜保護某方當事人合法權益”,[8]。《刑法》“偏重”的當事人是誰呢?回答是“人民”!這實在是一個太大的范圍。那么非偏重的當事人是誰呢?當然應當是“非人民”。如何界定“非人民”呢?正是這種以“單保護”與“雙保護”作為“任何一部法律或一個法律部門”的基本標志,將勞動合同法的立法宗旨引入了一個“非黑即白”的境地。
其次,舉出的一些“單保護”特點較為明顯的法律,恰恰不能證明勞動合同法屬于“單保護”范圍。“《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1條中‘保護消費者的合法權益’,《勞動法》第1條中‘保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9],這是“單保護”論者舉出的最有力的證據;然而,這一論據恰恰不能支持其觀點。作為消費行為,本身會受到兩部法的調整,即《合同法》與《消費者權益保護法》。按照“單保護”論者的分類,《合同法》是屬于“雙保護”范疇的。《勞動合同法》應當更接近屬于“單保護”的《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呢?還是屬于“雙保護”的《合同法》呢?鄭功成對于這一點的批評是:“勞動合同立法的核心內容,應當是以平等的立法理念,通過規范勞動合同的簽訂、履行、終止等程序和勞動合同當事人雙方的權利與義務,以及明確相應的行政監督與司法保障措施,來確保建立平等、健康、穩定、和諧的勞動關系,它是平等規范勞動關系的基本法律。”[10]按“單保護”論者的邏輯,勞動合同法似乎也是應當歸入“雙保護”范疇的。
最后,“單保護”論者最有力的論證就是,勞動合同法屬于勞動法,“勞動法區別于民法的根本標志是,勞動法基于勞動關系中勞動者是相對弱者的假設,在保護雙方當事人合法權益的同時,偏重保護勞動者合法權益,故立法目的條款中作‘單保護’表述。”[11]對于這一論證,也有人反駁:“《勞動合同法》不是勞動標準法,也不同于《勞動法》。《勞動合同法》是規范勞動合同當事人雙方權利義務的法律制度。”[12]
立法宗旨是一部法的生命線,有時一些學者也會將其視為劃定自己勢力范圍的標志。“《勞動合同法》的立法宗旨是保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它應該是保護弱者即勞動者的法律,經營者可以單獨立法。”[13]這種過度敏感多少讓人有些奇怪。無論“單保護”還是“雙保護”講的總還是勞動者與用人單位簽訂合同,勞動者要的是《勞動法》,經營者要的是《經營者保護法》。兩者簽訂合同時,用什么法呢?豈不是必然產生一部規范雙方或保護雙方的《勞動合同法》嗎?以一種極端的方式主張“單保護”觀點,卻導出一個完全的“雙保護”結論,這點可能是“單保護”論者始料不及的。
二、勞動合同立法宗旨之我見
依筆者看來,這場爭論最值得爭論的恐怕是“單保護”與“雙保護”的提法。勞動法學者似乎正在捍衛著勞動法的立法宗旨。因此,我們有必要搞清楚的是如何理解勞動法的立法宗旨,進而如何理解勞動合同法的立法宗旨。
現行勞動法是以合同化與基準化相結合的立法模式為依據來確定其立法宗旨的,必然從“傾斜立法”的視角來概括“保護勞動者的原則”。1994年公布的《勞動法》第1條以顯性的方式提出保護勞動者,同時通過強調“調整勞動關系”、“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勞動制度”;以隱性的方式提出保護用人單位,應當將其概括為“傾斜立法”。國家只是以基準法的方式為勞動關系確定底部,留出當事人的協商空間,并保障雙方當事人的平等協商。筆者早在1992年就率先將“保護勞動者”原則概括為“傾斜保護”[14],并于1993年依據這樣的指導思想參加了《勞動法》的論證和起草;在《勞動法》公布后的一系列著作中,筆者更有詳盡論述[15]。“傾斜保護”也漸成勞動法界的通論。
很多勞動法學界的同仁,以為“傾斜保護”與“單保護”是一回事。有人支持單保護原則,其理由是:“勞動法的立法宗旨突出維護勞動者合法權益。勞動合同制度是勞動法的核心,勞動合同法自然屬于勞動法,其立法宗旨當然要以勞動法為準,體現對勞動者的傾斜保護,而不是在形式上公平維護當事人雙方的合法權益。”[16]勞動法的立法宗旨確實是傾斜保護,但決不是什么“單保護”。傾斜保護作為勞動法的基本原則由“傾斜立法”和“保護弱者”兩方面構成。
一是保護弱者。就保護弱者而言,勞動法以一種特殊的標準衡量當事人的地位及分配利益。這些特殊的標準源于社會弱者的“身份”認定,是以特殊身份來決定利益的分配,使這種分配結果有利于具有“弱勢身份”的一方。表面看來,社會法似乎實行了一種“不平等”的“差別待遇”,其實這種“不平等”是針對社會關系本身存在的“不平等”;在社會法領域中,我們看到的滿眼都是勞動者、消費者、環境污染受害者、婦女、老人、未成年人、殘疾人這樣的弱勢群體。保護弱者的原則正是通過傾斜對于失衡的社會關系作出的必要矯正,來緩和這種實質上的不平等。這是另一種意義上的法律平等,即“實質平等”。
二是傾斜立法。傾斜立法將傾斜保護限定在立法上。這里有三層涵義:
首先,傾斜立法從內容上看應當集中體現在勞動基準法中,基準是指為了保障勞動者最起碼的勞動報酬、勞動條件而規定的最低限度的措施和要求。勞動基準法是有關勞動報酬和勞動條件最低標準的法律規范的總稱。用人單位可以優于但不能劣于基準法所規定的標準。凡集體合同、勞動合同、勞動規則(廠紀廠規)所確定的標準未達到國家規定的勞動基準的,均無法律效力。在我國,勞動基準法的內容主要包括工時、休假制度,工資保障制度,勞動安全衛生制度,女工、未成年工特殊保護制度。勞動合同法中也有相當一部分內容是屬于勞動基準法的內容。
其次,立法上可以在法律維護的利益上有所傾斜,但在司法上卻必須嚴守平等的原則;否則,如果將傾斜的重點放在司法上,由于法官“自由裁量”的尺度不同,就有可能形成新的利益分配不公。同時,賦予法官在司法上有“傾斜”的權力,也容易產生假借“公平正義”,作出恣意妄為的判決,就有可能危及正常的法治秩序。需要區別的是,有些司法制度的設計,本身是出于保護弱者的目的。以勞動監察制度為例,各國一般都將監察的范圍限定于雇主,而不對雇工進行監察。這是否是一種傾斜司法呢?其實這種向勞動者傾斜的司法設計,本身就是立法傾斜,在司法中仍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最后,在立法利益的分配上,也只是限定在“傾斜”上,仍給當事人的協商留出充分的余地。勞動法是私法與公法相互融合產生出來的法律。有些國家的勞動法可以是純公法性的,只將基準法的內容放在勞動法規范,而將私法規范規定在民法的雇傭合同中;我國法律部門的劃分是以社會領域為依據的,這一點是與國外的勞動法不同的,由此也決定了勞動法中應具有較強的私法因素。在我國,有民法學者稱“合同之精髓是當事人自由意志之匯合”[17],勞動法并不是要放棄這一精髓。臺灣學者蘇明詩指出:“各個人不分強弱、賢愚,均得以自己之意思活動,而社會之利益,亦當與其成員之個人利益相一致,故自由競爭,應為社會之最好指導原理。故個人主義與自由主義,應屬一物兩面。”[18]羅爾斯在其《正義論》一書中指出:契約的安排體現了一種正義,契約的原則就是“作為公平的正義”,它“正是構成了一個組織良好的人類聯合的基本條件。”[19]勞動法并不是要取消這種合同自由,而是要將這種合同自由限制在一定的范圍。勞動合同法在法律規范上,仍應強調任意性規范的重要性;這些任意性規范與民法相比,又有其自身的特點,受到勞動基準法中強制性規范的嚴格限制。
“勞動合同法立法宗旨”與“勞動法立法宗旨”相比較是種屬關系。“勞動法”是屬概念,“勞動合同法”是其種概念;或者說,“勞動法”是上位概念,“勞動合同法”是下位概念。種屬關系是指兩個內涵不同的概念,其中一個概念的外延是另一個概念外延的一部分。勞動合同法的立法宗旨確實從屬于勞動法,具有勞動法的性質。但勞動法本身是傾斜立法,具有私法與公法的特征,而在勞動合同法這部分內容中,應當是最體現其私法性特征的內容。因此,在立法特征的表述上,應當有私法特征的表述。勞動法的起草其實一直在社會法的范疇中進行,如果我們不故弄玄虛,把“雙保護”與“單保護”當做什么私法轉向社會法的標志;如果以傾斜立法作為一個基本出發點,就會發現,從字面上看,各方的分歧似乎并不大。
先看所謂“單保護”論者的觀點。這些學者有個結論性的歸納:“可見,保護勞動者與保護用人單位是‘一個硬幣的兩個方面’的關系。”[20]既然是“一個硬幣的兩個方面”,從這段論述的自身邏輯看,應該得出“雙保護”的結論,但是該作者卻主張所謂的“單保護”,筆者不知該文作者如何拿著“單面的硬幣”去購物。
再看所謂“雙保護”論者的觀點。“我國制定《勞動合同法》的目的,應當是平等保護勞動合同當事人雙方的正當權益,促進勞動關系平等、健康與穩定發展,它特別需要注重對勞動者正當權益的維護,但絕對不是只保護勞動者的權益而忽略用人單位或雇主的正當權益,絕對不是要偏袒勞動者,而是要確立勞動者與用人單位或雇主平等的法律地位,維護雙方的正當權益,最終實現用人單位或雇主與勞動者走向合作與雙贏,因此,它應當是一部符合用人單位或雇主與勞動者雙方共同利益的法律。”[21]可以看到,所謂“雙保護”論者并不反對側重保護勞動者。
正如有些勞動法學研究者所說,“單保護”與“雙保護”之說并無本質上的矛盾;“單保護”說并不意味著只保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而不保護或者排斥用人單位的合法權益。在現代民主國家,任何一部經過法定程序制定的法律都不可能以犧牲某一類社會主體的合法、正當權益來維護另一類社會主體的特權,法律的制定總是在利益相關主體之間尋求一個平衡點,以對社會主體之間的利益進行合理的分配,同時每部法律都體現了立法者一定的價值選擇。“單保護”是在對勞動者和用人單位雙方合法利益保護的基礎上,對勞動者給予一定程度的傾斜保護,并不是忽視對用人單位的合法權益的保護,不會導致勞動合同關系雙方主體的權利失衡[22]。
《勞動合同法》第1條最終的表述是:“為了完善勞動合同制度,明確勞動合同雙方當事人的權利和義務,保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構建和發展和諧穩定的勞動關系,制定本法。”顯然是兼顧了這兩個方面,我們不妨借用所謂“雙保護”、“單保護”的結構分析一下:“明確勞動合同雙方當事人的權利和義務”顯然是在強調用人單位與勞動者雙方各自有自己的權利義務,凡權利本身就是法律應當保護的,應算是“雙保護”的表達;“保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肯定應算是“單保護”的表達,如果要找一個統一的視角,那就是“傾斜立法”。《勞動合同法》的表達與《勞動法》的差異在于:《勞動法》第1條以顯性的方式提出保護勞動者,同時通過強調“調整勞動關系”、“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勞動制度”,以隱性的方式提出保護用人單位;《勞動合同法》的所謂“雙保護”與“單保護”都是以顯性的方式來表達的。這是照顧了勞動合同法特征,其應當比勞動法更突出私法的特征。
立法者并沒有進入學者給他們預先劃定的要么“雙保護”,要么“單保護”,只能兩選一的思維定勢中。傾斜保護的立法思路可以從以上分析中得到印證,這也是《勞動合同法》自身的特質決定的。
三、勞動合同立法宗旨爭論的深層思考
勞動合同立法宗旨中所謂“雙保護”與“單保護”的爭論是否只是一場由誤會引起的無謂的爭論呢?答案是否定的。隱藏在“雙保護”與“單保護”爭論背后的,其實是勞動合同立法中是否需要強調私法規范的問題。
持“雙保護”觀點的學者認為:“盡管基于中國強資本弱勞工格局的現實,勞動合同立法需要更多地關注對勞動者正當權益的維護,但勞動合同作為一種特殊的民事合同,勞動關系作為一種特殊的民事關系,其立法的宗旨仍然應當是‘平等’,即既要保護勞動者的正當權益,也要維護雇主的正當權益。”[23]可以看到,那些被概括為“雙保護”觀點的人大代表,往往都比較強調勞動法中的私法因素。
勞動合同法的討論是在一種特別的氛圍中展開的。這種特殊氛圍甚至使一些學者以“180度的大轉彎”來和過去的自己劃清界限。“有的觀點認為,勞動合同(或雇用合同)是一種民事合同,有的國家至今還將其納入民法的調整范圍,故勞動合同法應當像民事合同法一樣作‘雙保護’表述。其實,勞動合同作為從民事合同中分離出來的一種特殊合同,雖然具有合同的一般性,更有其基于勞動者是弱者的特殊性。勞動合同法(或雇用合同法)在有的國家雖然被納入民法體系,但處于民事特別法的地位,其‘特別’正在于勞動者的弱者地位和對勞動者的偏重保護以及為實現偏重保護而對契約自由的限制。故不能因勞動合同法被納入民法體系而否認其偏重保護的特征。而在我國,勞動合同法是勞動法的組成部分,更應當強調偏重保護。”[24]
在勞動法學界主張是“勞動合同(或雇用合同)是一種民事合同”的代表人物是王全興,這種觀點甚至構成其標志性的學術思想。“勞動法與民法之間是特別法與一般法的關系。法理學認為,在法律適用上,特別法優先于一般法,但一般法可以補充特別法。然而,我國法學界在討論勞動法與民法的關系時,只注重特別法優先于一般法,卻忽視了一般法補充特別法。”[25]
在勞動法學界主張“勞動合同作為從民事合同中分離出來的一種特殊合同,”應強調“具有合同的一般性”的代表人物也是王全興。“在勞資矛盾激烈的歷史背景下,勞動法從民法中分離出來具有必然性,而在勞資矛盾日趨緩和,特別是向勞資伙伴關系轉化的現代,勞動法似乎有了回歸民法的必要。”[26]
有媒體誤傳筆者主張勞動法回歸民法,其實筆者從來沒有贊成過這種觀點;而是王全興的觀點。從某種意義上看,正是為了和自己的標志性觀點劃清界限,王全興才特別強調“單保護”觀點,強調勞動合同法的特殊性。然而,正如馮彥君所言:“必須加以強調,勞動合同再特殊,勞動合同立法再體現制度個性,勞動合同也仍然是合同,勞動合同法也不可否定和排斥合同制度的基本共性,即制度普遍性。這種制度普遍性就是最基本的契約自由和合同主體的選擇空間。”[27]其實這恰恰是問題的關鍵。那些自稱為“單保護”觀點的學者將“傾斜立法原則”改換成所謂的“單保護原則”,并一再強調這是與民法區別的關鍵原則[28],實際上是要否定勞動立法中的私法性規范。這些學者在討論勞動合同立法時有一種觀點:“從立法假設的角度來看,勞動法是將雇主設定為侵害勞動者權利、引發勞資沖突的最直接主體而來構建法律體制的。因而,勞動法對于雇主而言更多的是限制而不是保護。對于企業或雇主的保護,主要是通過《企業法》和《公司法》等法律來實現的。”[29]
“單保護”觀點將勞動合同關系視為侵權關系。勞動合同立法本是規范勞動者與用人單位勞動合同簽訂、履行、變更、解除過程的法律,按照這種邏輯,這一過程也應當是侵權發生、變化、完成的過程。侵權責任是指侵犯了權利人的權利而產生的法律責任;侵權責任的產生,并不要求一個合約的存在,侵權過程一般也不會按事先的約定來完成。如果法律預先將雇主設定為侵權主體,勞動者設定為被侵權主體,勞動合同的合約安排就成為多余。侵權主體與契約主體有明顯的區別,侵權主體往往是因觸犯法律產生出來的應當承擔賠償義務的主體。用人單位在簽訂勞動合同時被預先設定為侵權主體、過錯主體,也可說是一種“原罪”,雙方當事人顯然并無平等協商的可能性。將契約關系改造成侵權關系,顯然將根本否定勞動合同簽訂的意義。
按照“單保護”學者的理解,勞動合同法,只保護勞動者,不保護用人單位;《企業法》、《公司法》則只保護企業、公司,不保護企業、公司中的勞動者。那么勞動者與用人單位兩者簽訂合同時怎么規范呢?有學者指出:“在這里,實際上遇到了兩種權利的沖突,即雇主的財產權和勞動者的生存權的沖突。在兩種權利發生沖突的情況下,作為社會法的一個基本理念即是生存權優位。”[30]很難設想一個國家為什么要做這樣的制度安排,面對一個雙方發生的行為,國家不去直接規范,而是故意搞兩套大面積沖撞的制度,然后以“生存權優先”作為一種“沖突規范”,來協調兩套制度的關系。這種理解也根本不符合勞動合同法“構建和發展和諧穩定的勞動關系”的立法宗旨。
“單保護”的觀點是極其有害的。當這些學者將勞動法的傾斜立法原則改造成“單保護”原則,將勞動合同關系理解為侵權關系時,就已經否定了雙方當事人可以通過任意性規范,以協商的方式對勞動關系的一些內容進行安排。盡管這些學者說自己主張的是社會法,但當立法將私法規范從勞動關系全部或者部分地抽走時,我們看到的實際上是一個完全公法化了的勞動關系。德國學者海因·科茨等指出:“私法最重要的特點莫過于個人自治或其自我發展的權利。契約自由為一般行為自由的組成部分……是一種靈活的工具,它不斷進行自我調節,以適用新的目標。它也是自由經濟不可或缺的一個特征。它使私人企業成為可能,并鼓勵人們負責任的建立經濟關系。”[31]“合同自由要求給予社會成員在訂約時自由選擇的權利,讓他們自己決定如何取得權利及其權利的讓渡。”[32]一旦勞動關系完全喪失活力,我國的經濟體制也必將開始走回頭路。
所謂“雙保護”觀點,很大程度上是學者對立法過程中人大常委會常委觀點的一種概括。這些常委在論述時,基本上都是從勞動合同是民事合同的一種特殊類型來進行論述的,強調兩者的共性。很少有人從社會法中也應存在著私法因素來進行論述。筆者不贊成勞動合同是民事合同的一種特殊類型的說法,這種觀點很容易引向以純私法的觀點來解讀勞動合同法。“當我們的民法、合同法教科書還在津津樂道于闡述具有古典平等、自愿和公平色彩并略帶幾許早期交易烙印的合同法的概念的時候,當我們的合同法還堂而皇之地將合同定義為雙方當事人協商一致產物的時候,現實經濟生活中的合同實踐卻沖破法學家們的理性約束和國家的立法框架,用定式合同開辟了自己新的發展道路。只要稍微留意就會發現,原來我們訂立的合同很少是協商一致的產物,而是由對方一手操縱的。”[33]我們不能以純私法的觀點來規范、起草勞動合同法,畢竟我國的勞動合同法是基準法與合同法的整合,是公法因素與私法因素的整合。依筆者看來,這些人大常委會常委并不反對國家的適度干預,只是認為應當給勞動關系留出契約的空間,其實這是社會法的典型思維。可惜的是,我們很多勞動法的研究者在講社會法時,私法因素只是擺設,將社會法宣傳成了行政法。
可見,脫離了傾斜保護去談“單保護”或“雙保護”,只會使勞動法成為民法或行政管理法。勞動合同立法應當從傾斜保護出發來認識其立法宗旨。《勞動合同法》立法宗旨的表述,在承繼了勞動法立法宗旨的基礎上集中突出了勞動合同法中私法的因素,能夠使我們對傾斜保護的社會法思路進行重新的認識。
注釋:
[1]王全興.勞動合同立法爭論中需要澄清的幾個基本問題[J].法學,2006(9):19—22.
[2]常凱.關于勞動合同立法的幾個基本問題[J].當代法學,2006(6):32.
[3]佚名.關于立法宗旨——分組審議勞動合同法草案發言摘登(二)[EB/OL].(2007—04—29)[2007—07-15].
[4]見驚雷.厲無畏建議:競業限制補償標準作進一步研究[EB/OL].(2006—03—24)[2007—04—22]
[5]王全興.勞動合同立法爭論中需要澄清的幾個基本問題[J].法學,2006(9):19—22.
[6]關懷.《勞動合同法》與勞動者合法權益的保護[J].法學雜志,2006(5):8.
[7][8][9]王全興.勞動合同立法爭論中需要澄清的幾個基本問題[J].法學,2006(9):19—22.
[10]鄭功成.勞動合同法不是偏袒勞動者的法律[J].光明日報,2006—04—24;
[11]王全興.勞動合同立法爭論中需要澄清的幾個基本問題[J].法學,2006(9):19—22.
[12]程多生.《勞動合同法》的立法宗旨必須堅持維護勞動合同當事人雙方的合法權益[J].中國勞動,2005(12):8.
[13]李小彤.觀點交鋒:勞動合同法立法背后的利益博弈[EB/OL].(2007—03—20)[2007—07—27].
[14]董保華,程惠瑛.中國勞動法學[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2:80.
[15]董保華.勞動合同研究[M].北京:中國勞動社會保障出版社,2005:423.
[16]姜穎.對《勞動合同法》立法的幾點認識[EB/OL].(2006—03—20)[2007—05—31].
[17]王家福.民法債權[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1:266.
[18]蘇明詩.契約自由與契約社會化[C]/鄭玉波.民法債編論文選輯:上冊.臺北:臺灣五南出版社,1985:166.
[19]約翰?羅爾斯.正義論[M].何懷宏,何包鋼,廖申白,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5.
[20][24]王全興.勞動合同立法爭論中需要澄清的幾個基本問題[J].法學,2006(9):19—22.
[21][23]鄭功成.勞動合同法不是偏袒勞動者的法律[J].光明日報,2006—04—24;
[22]林嘉.勞動合同法:突出保護勞動者是對不平等的矯正[N].了人日報,2007-05—21.
[25][26]王全興.勞動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43.
[27]馮彥君.我國勞動合同立法應正確處理三大關系[J].當代法學,2006(6):26.
[28][29][30]常凱.關于勞動合同立法的幾個基本問題[J].當代法學,2006(6):32.
[31]羅伯特?霍恩,海因?科茨,漢斯?萊塞.德國民商法導論[M].楚建,譯.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6:90.
[32]陳林林.合同法上違約金制度檢討及其改進[J].江海學刊,1999(1):67.
[33]張新寶.定式合同基本問題研討[M]//姚輝.民法的精神.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