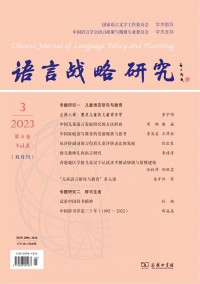語言翻譯
前言:本站為你精心整理了語言翻譯范文,希望能為你的創作提供參考價值,我們的客服老師可以幫助你提供個性化的參考范文,歡迎咨詢。

[摘要]翻譯不僅是語言之間信息轉換的文化活動,而且是一系列復雜的思維活動。意識形態以不同的語言形式隱藏在語篇之中,以各種隱蔽方式潛移默化地影響著作者寫作、譯者翻譯以及讀者解讀文本。本文擬以批評語言學為主要方法論,強調翻譯中語言分析和社會分析相結合的重要性,同時主張翻譯研究應以語篇為單位。特別注意考察作者、譯者、讀者在翻譯過程中的三元關系及其在意識形態的建構、解構、重建和解讀過程中的作用。以便弄清翻譯的本質并有效地解釋那些“不忠”的現象。
[關鍵詞]意識形態;翻譯模式;翻譯研究;翻譯過程
一引言
翻譯研究往往側重探討翻譯結果,忽略了對翻譯過程的研究,對意識形態在翻譯過程中的作用更是避而不談;翻譯評論、翻譯理論始終拿著“忠與不忠”的尺子來衡量所有翻譯作品。20世紀80年代以來,意識形態被引入翻譯研究,有關意識形態和翻譯研究的討論如火如荼,真可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研究意識形態對翻譯的作用不僅有助于我們認清翻譯的本質,而且有效地解釋了那些“不忠”現象。這樣也有利于提高翻譯工作者對意識形態的認識,也可使翻譯批評家和研究者從意識形態、歷史、文化諸角度客觀地審視譯作,深入分析該譯作產生的歷史文化背景等特點,而不是簡單地對比原作和譯作,匆匆做出“忠”與“不忠”的草率結論。
翻譯研究是一項十分復雜的活動:首先,翻譯不是單純的抽象思維,而是一種包括抽象思維和靈感思維在內的錯綜復雜的思維活動。意識形態影響翻譯的全過程,但方式不同、角度不同,效果也各異。這種影響有時候是顯性的,有時候卻是隱性的,不易覺察。翻譯研究要考察作者、譯者和讀者這三類人的意識形態在整個翻譯過程中的活動規律以及所發揮的作用。其次,翻譯研究還要涉及文學、語言學、心理學、認知科學、符號學、美學、傳播學、跨文化交際等諸多學科。最后,應該了解片面地強調某個方面是不科學的,翻譯研究要在語篇環境下進行全面研究,因為語篇是意識形態發揮作用的基本條件。
批評語言學以功能語法和社會語言學等學科為理論基礎,認為語言是一個系統,在作者創作、譯者翻譯的過程中,受意識形態的支配,會有意識、無意識或者下意識地從各自語言系統中選擇一定的語言形式。那么,在一定條件下,不同的語言形式會發揮不同的語言功能,不同的語言功能也將產生不同的社會效果。意識形態就是這樣以不同的語言形式隱藏在語篇之中,以極其隱蔽的方式發揮作用。本文擬以批評語言學為方法論,旨在揭示:意識形態在翻譯全過程中是如何發揮作用的?
二意識形態及其對翻譯的作用
1796年法國哲學家D.deTracy首創了“ideologie”一詞,用來表示一種負有使命的“觀念學科”,作為世界觀和哲學思想的主體,對宗教進行現代批判。其目的是為人類服務,甚至拯救人類,使人們擺脫偏見,以便為理性的統治作好準備。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指出,“意識形態”是由虛假觀念所組成的,它們顛倒了社會意識和社會存在之間的關系,掩蓋了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掩蓋了社會生產方式內部的矛盾、運動、變化和發展需要說明的是,意識形態的這種歪曲的性質,不是某個思想家任意所為,而是取決于一定的社會存在和社會關系的性質。所以,社會現實在意識形態上的反映,不能簡單地歸結為社會現實的虛假觀念;這種反映具有實在的、客觀的內容,雖然這種內容是被歪曲地表現出來的。
盡管“意識形態”在馬克思主義詞典中已經有了明確的界定,但是經歷了現代和后現代的思想洗練之后,似乎難以做出一個公認的適當定義了。由此看出,這一經典已經被人篡改或淡化。從另一個角度講,說明意識形態也與時俱進,不斷適應深化的社會生活。隨著時代的發展,意識形態涵蓋了科學在內的整個文化領域,成為人類認識世界的一個必不可少的中介。意識形態可以是某一階級、政黨、職業內的人對世界和社會的有系統的看法和見解,也可以是某一國家或集體里流行的潛藏在政治行為或思想風格中的信念;同時,一個人在一定時期內的一整套或有系統的社會文化信念和價值觀也屬于意識形態的范疇。具體表現形式為哲學、政治、藝術、審美、宗教、倫理等。所以,我們要全面、客觀地認識意識形態,不為某種觀念所左右,否則,就會做出錯誤的結論。
翻譯操作學派的A.Lefevere將意識形態引入翻譯研究,認為意識形態是“一種觀念網絡,它由某個社會群體在某一歷史時期所接受的看法和見解構成,而且這些看法和見解影響著讀者和譯者對文本的處理”。因此,翻譯不是一個簡單的語言文字轉換過程,而是一種文化政治行為。那么,譯者首先要服從的不僅僅是原文,更多是目的語文化中的意識形態、道德規范、審美觀念等。譯者作為社會的人,處于一定的社會階層,其意識形態受到一定上層建筑的控制,因此其翻譯行為是為該階級的利益服務的,具有強烈的意識形態傾向。再者,譯者實際上還擔負著跨文化交際的使命,在其翻譯過程中將一種異域文化的話語所包含的觀念、價值觀、意識形態等引入本土文化。除此,翻譯也受到社會單位的權力和意識形態的限制;譯作還要迎合讀者的主流意識,否則就不得不對其進行加工處理。
批評語言學認為,“意識形態”一詞并無“虛假”或“歪曲”的含義,是指“人們安排或證明自己生活的方式”或“人們生活和向自己表現其與生存環境的關系的方式總和”。批評語言學主張,語言分析要和社會分析相聯系。然而,意識形態表現得非常多樣化,而且隱蔽性較強,不易被覺察。因此,我們要特別注意意識形態的這些特點,這樣有助于我們把握意識形態的本質及其對翻譯的影響。21世紀是個多極化世界,多元文化并存的局面是不可避免的,社會生活將會更加全球化和信息化。任何封閉的思維或措施都是沒有出路的,甚至是不可能的。人們的思想、觀念、行為等都發生了變化,意識形態的表現形式也在變,當然對翻譯的要求也要隨之變化,否則那種不合時宜的翻譯就必然會被淘汰。批評語言學的出現給我們提供了研究意識形態、語言以及翻譯的新視角。
三翻譯模式研究
蘇聯翻譯理論家L.Barkhudarov認為,翻譯包括兩個層面:翻譯過程和翻譯結果。在翻譯過程中,決定著翻譯策略、翻譯結果的是譯者所選擇的翻譯模式。所謂翻譯模式,就是對整個翻譯過程所作的概括性描述,也是對翻譯活動規定的一套標準的操作程序。翻譯理論家一度提出種種翻譯模式,目的是為了描述真實的翻譯過程,弄清楚翻譯的實質。但往往比較重視對翻譯結果的研究,而忽略了對翻譯過程的研究。翻譯過程不僅涉及語言學以及與語言密切相關的社會文化等諸多因素,還涉及了作者、譯者和讀者的個性、生理、心理問題、意識形態的活動等,因而顯得十分復雜。而人對自身的了解,尤其是對大腦機制的了解十分有限,這樣就限制了對翻譯過程中思維活動的深入研究,這也是目前許多翻譯理論對翻譯模式構造的不夠完整的原因。
翻譯模式發展初始階段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代表人物E.A.Nida認為:首先譯者應該從語法和語義層面對原文的表層結構進行“分析”,以便進入原語的核心層次;然后將分析后得到的各種信息進行處理,將其從原語“轉換”為譯語,并弄清原語與譯語核心句之間的內在聯系以及譯語可能出現的各種表達形式;最后譯者根據譯文的需要,把傳遞過來的信息進行“重組”,以一定的譯語形式將其固定下來。Nida模式顯然受到結構語言學的影響,主要是從信息等值角度考慮翻譯問題,將語言形式與語言內容分離,只注重語言對比,忽視了非語言因素、使用語言的人以及其思維活動的研究,因此難以全面解釋翻譯過程,但是此模式引入表層、深層結構分析語言轉換的過程,為建構翻譯模式奠定了基礎。鞏固階段的代表W.Wilss首次提出:翻譯的第一個階段是“分析”,即譯者對原文文本的主要意圖和修飾進行仔細思考,然后是第二階段用譯語“重現”原文意圖。此模式說明,該理論比前人有所進步,Wilss認識到翻譯時譯者的思考活動與翻譯結果密切相關,并將分析原文看作翻譯過程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提出要考慮原語的語義和修辭,但卻沒有考慮文化、語境等因素,也沒有深入探討思維活動的過程。深入階段R.T.Bell根據心理語言學和人工智能的研究成果,系統地借用了語義學、語用學、語篇分析、功能語法和信息論等學科的基本原理,對翻譯過程進行了研究并提出了翻譯的心理模式:“原語語篇分析過程”(語法分析-語義分析-語用分析-語義表達);“語義表述綜合過程”(語用綜合-語義綜合-句法綜合)。該階段翻譯中多學科分量加重,對翻譯過程中大腦的思維活動做了有意義的研究,從而使得對翻譯模式的描述和規定也進一步接近翻譯的實質。該理論涉及翻譯本質、翻譯心理過程、譯文評價標準等方面,是一種理論基礎扎實、內容完備的多學科理論。這是貝爾對翻譯的最大貢獻。
翻譯是個十分復雜的過程,需要考察作者、譯者、讀者這三類人,要認真分析意識形態的建構、解構、重建和解讀四個環節。翻譯研究不僅要研究原作和譯作而且研究人,因為人的社會地位決定意識形態,翻譯中語言形式選擇受到意識形態的驅使,那么所產生的社會功能也是不一樣的。意識形態是一定社會和文化的產物,翻譯作為一種跨語和跨文化交際行為,從一開始就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意識形態的烙印。譯者在將一個異域文化的話語所包含的觀念引入本土文化時,必然會對這來自異域文化的價值觀做出自己的價值判斷,然后決定傳達策略。批評語言學主張,語言研究要在語篇、語境環境中進行,不僅要研究語言還要研究人和人的意識形態。這是語言研究的進步,也給我們探討翻譯過程中意識形態的活動提供了一定的理論依據。
四意識形態的建構、解構、重建與解讀
(一)意識形態的建構
原文的寫作過程是一個思維過程,是意識形態建構并發揮作用的重要階段之一,然而這一階段卻一直被翻譯研究所忽視。根據Sapir-Whorf假說,思維是通過語言來感知外部世界的,而語言并非是一個透明的中介,它可能歪曲現實,從而影響并控制思維,控制人們對世界的主觀體驗。一方面,文化不同,思維不同,語言結構也就不同(語言相關論);另一方面,語言不同,思維、文化也就不同,語言結構就影響人的思維結構(語言決定論)。所以,翻譯僅僅研究作品本身是遠遠不夠的,還需要考察作者在寫作過程中的思維活動。因為作者身處一定的社會階層,其意識形態、思想內涵、寫作方式等都受到一定的文化熏陶,這些東西是潛移默化的,在寫作中會自然而然地發揮出來,有時候也許作者自己也渾然不知。寫作過程中的素材選擇、人物刻畫、遣詞造句、篇章布局等都與意識形態的作用不無關系。
從篇章結構而言,每一種語言都有其獨特的方式來表達思想感情,語篇結構和其中的語言形式是作者在其交際目的和意識形態傾向以及其他各種社會因素的作用下,從整個語言體系中篩選出來的。這些模式都有一定的定式,無一例外地受到意識形態的擺布。作者有意無意間選擇了不同的語言形式來表達自己的情感,而這些語言形式一旦出爐就不是簡單的語言形式了,就會發揮一定的語言功能,從而產生一定的社會意義。當然,原作中作者選擇的某種語言結構孤立來看也許并不帶有任何社會意義,然而一旦它頻繁地出現于特定語篇和語境中或者當它與其他結構相結合時,便可能產生重要的意識形態意義。
就語篇體裁而論,一種語言中的各種體裁都具有特定的意義潛勢,包括具體的語義范疇、主體位置、修辭方式、使用規則和慣例等;它們代表著不同社會階層的利益,適合于表達不同社會群體和機構的意識形態。這樣一來,作者實際上無形中運用了語言的適當形式向譯者和讀者灌輸了自己的意識形態。然而,原作語篇中的意識形態意義并不一定都是作者有意識表達的,相當一部分源于語篇體裁和語篇類型的意義潛勢,這種意識形態意義往往是由于說話人的文化背景、所受教育、所處社會階層和地位、所從事職業和所代表的利益等因素所不由自主地或無意識地表達出來的。這也恰好反映了意識形態潛移默化塑造人的強大威力,而這種威力首先和主要是在人的社會化過程中通過語言和語篇發揮作用的。所以,考察作者寫作中意識形態的活動是非常重要的,也是翻譯過程中必不可少的準備階段。如果我們仍然忽視原作者的意識形態活動,那是不負責任的。
(二)意識形態的解構
批評語言學吸收了法國哲學家Foucault的后結構主義思想,認為意識形態在語篇中普遍存在。“語篇是在語言的外殼下起操縱作用的社會化的意識形態。語言只是語篇的形式,意識形態才是語篇的內容。任何一種語義內容都有無數種語言形式可選擇,選擇是由意識形態決定的,是在不同的語境下,不同的目的決定的結果。內容決定形式,意識形態決定語言再現形式的選擇(即意識形態對語篇的決定性)。”因此,翻譯中意識形態的解構是個十分復雜的過程,要研究多個層面,考慮許多因素。不能單純地分析語言形式,要在語篇、語境條件下分析語言形式,斷章取義就會產生誤解,出現錯誤。
翻譯的解構是以語篇環境為基礎,以語篇分析為渠道。語言的使用是從音、形、義等方面的代碼特征系統中做出選擇,創造出可以傳遞意義的語篇。關于語篇分析的復雜性,立體語言學普遍語法模式的初步設想可以提供佐證:語言符號系統的結構可按等級(音素、詞素、詞、詞組、句、超句體、篇章)和層次(表層、修辭層、深層)縱橫切分成具有組合關系和聚合關系的二十一個語言平面。對于譯者來說,了解語言特征(方言特征和使用標記),尤其是了解語言的使用標記,是非常必要的。因為翻譯過程的第一步就是語篇分析,而語篇參數是分析的重要依據。譯者首先要辨認出語言使用的各種標記,其次要與社會因素緊密聯系:1)交際者的身份及其之間的關系;2)根據語篇的目的(功能)選擇語篇的表現方式;3)語篇所涉及的(發生在社會上某個領域的)事情。此外,譯者還要對兩種語言的(音、形、義)特征了如指掌,才能在語言的特征系統中做出選擇,創造出一個和原文基本等值的語篇來。
傳統語言學模式指導的翻譯只研究語言,其重點在句子,認為詞與句決定意義,把翻譯對等的概念簡單地建立在詞、句層面上。這種“自下而上”的過程生產出來的譯品,很難被目的語讀者認同。語篇語言學主導的翻譯研究方法是對傳統語言學途徑的發展,側重語篇分析和語用意義,其研究對象不僅僅是原文和譯文兩種語言體系,而且還包括言外因素“情景語境”和“文化語境”。這種模式把翻譯看作是一個“自上而下”的過程,即先決定譯文在目的語文化中的屬性或類型以及其交際功能,再通過一個個的語言結構體現預定的語篇。其分析方法是:以整個語篇為重點,認為意義通過語言結構來體現,把翻譯對等建立在語篇和交際層面上。主張在翻譯實踐中建構一個適用于目的語社會的語篇,并不是依賴表層結構(句與句)的轉換,而是自上而下地、有目的地解構原文并為重寫整個語篇做準備。
批評語言學是一門開放的學科,其方法論主要建立在Halliday的系統功能語法之上,但也不排斥其它語言理論中適用的概念和方法。其基本原則是:語言有三個主要功能,即概念功能、人際功能和語篇功能。那么,譯者在分析語篇時,可以把其中的每個語言形式和過程與這些功能相聯系;在對語篇進行批評性分析時應該特別注意考察及物性、情態、轉換、分類、連貫性等蘊含的意識形態意義。Fowler認為,原文語篇的結構和所選擇的語言形式是作者在各種社會因素和話語目的指導下,從整個語言體系中遴選出來的,因此它們具有重要的社會意義或意識形態意義。這并不意味著這些語言結構與意識形態有什么固定聯系,但它們的出現在特定語篇中,并與其它結構相聯系,便可產生重要的社會意義。這也不是說作者在寫作中總是故意利用各種表達形式來歪曲事實,欺騙譯者和讀者,以達到某種個人目的。在通常情況下,甚至作者本人也未必意識到自己的話語中含有某種意識形態意義,譯(讀)者對此也渾然不覺。事實上,人們在進行言語交際時必須借助的頭腦中帶有階級烙印的圖式知識和意識形態成分,大多已經自然化為非意識形態的模式了。這正是意識形態的效力所在,它以潛移默化的方式使人們在不知不覺中傳播它,強化它。Fairclough指出,“意識形態通過偽裝自己的性質,裝扮成它不是的東西發揮作用”,其作用方式是最隱蔽時才最有效。批評語言學的目的就是,要通過語篇分析來揭示語言中這種含而不露的意識形態意義及其與社會結構和權力控制的關系。
(三)意識形態的重建
意識形態的重建過程是翻譯目的的實現過程,意識形態從此獲得新生。翻譯就是有目的地選擇語言資源,對整個語篇進行重寫,重建一個適用于目的語文化的語篇。毫無疑問,原作語篇被譯者解構得支離破碎,要是符合目的語的意識形態要求,就有可能保留下來;不符合就會擺脫原作意識形態的約束,這樣就使得改寫成為必然。在此期間,譯者要依靠一定的意識形態將兩種文化的碎片整理出來,要改變原有的詞序、話語順序、邏輯結構等,為形成一個嶄新的語篇做好準備。由于譯者屬于某個社會階層,所以這種意識形態的重建可能反映出某種意識形態傾向,與作者的意識形態再次發生碰撞。譯者要將這兩種格格不入的意識形態融為一體,需要對原作意識形態進行本土化改造,其手法或者是顯性的,或者是隱性的。
翻譯過程是譯者與作者之間意識形態的對話,語篇翻譯的條件就是在譯者與作者達到某種“理解”的基礎上對原文進行二次“寫作”或“創作”。這種“理解”的基礎是,兩者在人生觀、價值觀、藝術觀、創作風格,甚至在天賦、人生體驗和情感世界上的共同點;共同點越多越容易溝通。只有具備了與原作者這些相似條件,譯者才會選擇某個原作者的作品,也容易表達出類似的情感;譯者在理解過程中才能夠站在整個語篇的高度準確把握作者的思想感情、創作動機、寫作風格、言外之意等等。此時,譯者既要考慮原文和譯文兩種語言體系的差異,也考慮語言體系之外的各種制約因素,包括“情景語境”和“文化語境”。Neubert&Shrevet認為,在動手翻譯之前,譯者的腦子里首先有一個“虛構的譯本”,在翻譯的過程中,譯者“對語言的選擇受控于譯者腦子里的‘虛構譯本’;目的語中的資源為虛構譯本轉變為真實譯本提供了材料”。在實際翻譯中,譯者勢必會進入一種類似創作的狀態,充分發揮使用母語“寫作”的才能,對原作進行“二次寫作”。譯者的寫作以準確再現原文語篇交際價值和轉換整體藝術效果為最高使命,絕不會拘泥于原文個別字詞之間,甚至會脫離原文的形式。而譯者的寫作最終為原作語篇交際價值和整體藝術效果在譯語文化中的重現增添新的藝術魅力。從這個意義上講,翻譯中譯者的“寫作”頗具合理性和必要性。
語篇翻譯把翻譯對等的概念建立在語篇和交際層面上,并非詞、句層面上的表層結構轉換,所以翻譯一定程度上脫離了原作文本,譯者可以無所顧忌地進行改寫,而在此過程中文化是突出或掩蓋意識形態最為有效的方式。英國翻譯家D.Hawkes為喜愛小說的真正讀者而“寫作”《紅樓夢》的做法,也證明了語篇翻譯有目的地選擇語言資源對整個語篇進行“重寫”的合理性。Hawkes所譯《紅樓夢》(AStoryoftheStone)一經企鵝出版公司出版,頓時成為經典譯著。譯界稱道Hawkes運用譯語的高超及其文體價值的傳譯手段,普遍認為該譯本達到了文學翻譯的最高境界——“化”,在很大程度上能使人獲得接近閱讀原著的享受。
(四)意識形態的解讀
任何翻譯作品,只有迎合了讀者趣味才算是成功的,因為讀者才是譯作的最終檢驗者。然而,讀者對譯作的欣賞以及對作者和譯者意識形態的解讀方式是誰也想象不到的。相比而言,作者與譯者、譯者與讀者更容易溝通,因為他們之間有種特殊的親近感,這也是意識形態的功效使然。如果譯者選擇了原作、讀者接受了譯作,那就說明:讀者與譯者以及作者的意識形態達到某種程度的共鳴;譯作不僅促進了作品與讀者之間的文化交流,同時賦予原作一種新的實現。從這個意義上講,原作不僅產生了效果,而且獲得了第二生命。
任何譯作的出現都要經歷兩次“叛逆”:譯者對原作的解讀及其翻譯是第一次“叛逆”,而讀者閱讀譯作又經歷了一次“叛逆”。原作經過這種“創造性叛逆”獲得了“第二生命”,擴大了其被閱讀與接受的范圍。在傳統的翻譯研究中,“譯者”被貶低為“叛徒”而得不到人們的重視。但是在文學翻譯中,“創造性叛逆”一語卻是對譯者的一句贊語,是對譯作的文學價值的一種肯定。
在整個翻譯過程中,譯者不僅是原作的讀者,而且又是原作生命的延續者——譯作的作者,他通過自己對原作的理解,對原作進行再創造。他不僅是文化傳播中的接受者,同時也是輸出者,他的作用遠遠超出了一般的讀者。所以,有人把翻譯看作譯者的“誕生”與原作者的“消亡”,從而突出了譯者在翻譯這種文化傳播中的地位。譯者在選擇需要翻譯的作品時,除了受時代背景、讀者的需要等諸多因素的影響外,還與自己的喜愛及藝術風格等的借鑒有關。這就是譯者對原作的一種“選擇性共鳴”。這種“共鳴”為讀者提供了研究這些作家的思想乃至所受影響的種種可能,也為目的語輸入了新的思想、新的內容、新的文體、新的語匯等等。
五結束語
綜上所述,翻譯研究與翻譯實踐都不能單純地研究譯文,還要研究文本以外的東西,與翻譯有關的原文和譯文的語境以及作者、譯者、讀者的意識形態活動都應該是研究的對象。尤其是我們要通過語言現象,透視這些人在與語言接觸的過程中其意識形態是如何發揮作用的,因為意識形態以各種隱蔽的方式影響著作者的寫作、譯者的翻譯和讀者對文本的解讀。
翻譯是譯者在具有不同規則的符號系統之間進行信息傳遞的文化活動,體現了作者、譯者、讀者之間的三元關系。其過程是:作者←原著←譯者→譯著→讀者。可以看出翻譯是一種從譯者到作者又到讀者的活動。原作者是信息的發出者,譯文讀者是信息的接收者,而譯者則是以譯文為載體向讀者傳達信息的傳遞者,譯者是主體。譯者既要忠實于原作者又要服務于譯文讀者,所以有人說譯者是“一仆二主”。這樣的翻譯,自然不是單純技術性的語言外型的變異,而是要求譯者通過原作語言外型,深刻地體會了原作者藝術創造的過程,把握住原作的精神,在自己的思想感情、生活體驗中找到最適合的印證,然后運用適合于原作風格的目的語語言模式,把原作的內容與形式準確無誤地再現出來。這樣的翻譯過程,是把譯者和原作者合而為一,好像原作者用另一國文字寫自己的作品。這樣的翻譯既需要譯者發揮創造性,而又要完全忠實于原作的意圖。在充分理解了原作之后,譯者下面所面臨的任務就是要把原作品用譯語表達出來。這是一個再創作的過程,譯者要把得之于心的形象用譯語重新再現出來。在這一過程中譯者要把譯文讀者這一因素考慮進去,在進行判斷和作決定的思維活動中,要把讀者放到一個相當重要的位置上。
翻譯是戴著腳鐐手銬跳舞的尷尬角色,由于意識形態的引入和語篇翻譯法使得翻譯得到了解放。這樣一來,使得譯者加深了對原作的理解和更好地把握對譯作的處理,也使讀者更加理解譯者的被動處境。由于種種主觀和客觀因素,譯者對原作的理解不可能與作者寫作時的意向完全吻合;同時由于語言不同,譯者的表達方法也不可能與作者的表達方法毫無出入。即使語言相同,但同一原文在具有不同意識形態的譯者手里,譯文差別會很大。譯作不是一面鏡子,也不是原作的復制品,不可能把原作所反映的內涵和外延一板一眼地反射過來。翻譯如果能夠使讀者的感受與作者寫作時的感受達到近似或酷似的程度,就可視為成功之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