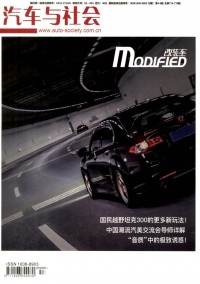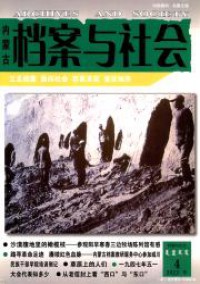社會(huì)正義和道德意識(shí)
前言:本站為你精心整理了社會(huì)正義和道德意識(shí)范文,希望能為你的創(chuàng)作提供參考價(jià)值,我們的客服老師可以幫助你提供個(gè)性化的參考范文,歡迎咨詢。

摘要:社會(huì)正義是政治哲學(xué)永恒關(guān)注的重要問題。長期以來在這一問題解決的思路上,逐步形成了制度與人心二元對立的中西兩極思維。特別是近代以來中國社會(huì)在西學(xué)東漸和中國文化自覺更新的過程中,不經(jīng)意間逐步形成的僅訴諸制度安排的合理性實(shí)現(xiàn)社會(huì)正義的單極思維幾乎成為一邊倒的話語霸權(quán)。這一傾向,人為割裂了制度安排與人的道德意識(shí)覺悟的內(nèi)在密切關(guān)聯(lián),從根本上忽視了作為歷史主體的人的道德意識(shí)覺悟?qū)τ谏鐣?huì)正義及其實(shí)現(xiàn)的重要意義,也無視中國傳統(tǒng)哲學(xué)道德理性思維對于社會(huì)正義及其實(shí)現(xiàn)的積極價(jià)值的歷史事實(shí),沒有注意汲取東亞社會(huì)成功地協(xié)調(diào)制度理性與道德理性的積極經(jīng)驗(yàn)。當(dāng)下的現(xiàn)實(shí)和學(xué)理的應(yīng)然,從一定意義上要求人們更加重視人的道德意識(shí)覺悟?qū)τ谏鐣?huì)正義及其實(shí)現(xiàn)的意義,從而確保制度安排的科學(xué)合理性與道德意識(shí)的理性自覺相得益彰。
關(guān)鍵詞:社會(huì)正義;道德意識(shí);制度安排;中國哲學(xué)思維;西方哲學(xué)思維
Abstract:Socialjusticeisaneternalpoliticalandphilosophicconcern.However,intheprolongedtheoreticaldiscussiononthisissue,adualistic-oppositionthinkingofinstitutionandmindhastakenshapebetweeneastandwest.EspeciallyinthemoderncourseofgradualwesternizationofChinesesocietyandself-consciousupdatingofChineseculture,thediscoursemonopolyhasunintentionallyshapedinwhichsocialjusticeberealizedonlybymeansoftherationalityofsocialinstitutions.Thistendencydeliberatelycutsoffthecloselinkbetweeninstitutionalarrangementandhumanmoralconsciousnessandcompletelyignoresthegreatimportanceofmoralconsciousnessofpeopleashistoricalsubjectstosocialjustice.Atpresent,itistheoreticallynecessaryandobligatorythatmoreattentionbepaidtothesignificanceofhumanmoralconsciousnesstosocialjusticeanditsrealizationtoassurethescientificrationalityofinstitutionalarrangementandrationalself-consciousnessofmoralsense.
KeyWords:socialjustice;moralconsciousness;institutionalarrangement;Chinesephilosophicthinking;westernphilosophicthinking
在政治哲學(xué)一向關(guān)注的重心——社會(huì)正義問題上,中國傳統(tǒng)哲學(xué)思維與西方哲學(xué)特別是西方現(xiàn)當(dāng)代哲學(xué)思維的理解和解決方案幾乎大相徑庭。前者希望訴諸人的內(nèi)在心性的道德覺悟,后者則追求外在制度安排的科學(xué)合理性,從而形成中西、古今兩極思維。近代以來,隨著西學(xué)東漸和中國社會(huì)全面走向現(xiàn)代化的進(jìn)程,我們自覺向西方學(xué)習(xí),對于西學(xué)的新思維幾近趨之若鶩。于是,在社會(huì)正義及其實(shí)現(xiàn)問題上,自覺不自覺地有把西學(xué)的制度理性安排視作惟一出路的思想傾向。這種傾向的不斷強(qiáng)化會(huì)以矯枉過正的姿態(tài)視中國傳統(tǒng)哲學(xué)以心性義理的道德意識(shí)覺悟的方式解決社會(huì)正義問題的思想資源為完全無用之說。這就人為地夸大了中西文化及其思想方法的差異,形成制度與人心二者必居其一、不可同日而語的思維悖論。但事實(shí)上,當(dāng)我們冷靜理性地反思和研究社會(huì)正義問題時(shí)將會(huì)發(fā)現(xiàn),制度與人心不僅不是非此即彼的簡單線性邏輯關(guān)系,更不是此消彼長的絕對對立關(guān)系,而是兩者密切地內(nèi)在關(guān)聯(lián),作用上相得益彰,邏輯上相互補(bǔ)充的關(guān)系。其中任何一方都不是萬能的,都不能獨(dú)立地對于社會(huì)正義及其實(shí)現(xiàn)起到完滿的作用。
一、唯制度理性論的缺失
社會(huì)正義問題在當(dāng)今的全球化時(shí)代顯得尤為重要。從國際社會(huì)的秩序看,全球化呈現(xiàn)出的政治多極化與霸權(quán)主義單邊政治思維的抗衡、經(jīng)濟(jì)全球化與后發(fā)展國家地區(qū)被邊緣化的矛盾、文化多元化與相對主義陷阱的困惑等,在學(xué)理意義上都表現(xiàn)為世界秩序的社會(huì)正義問題;就國內(nèi)社會(huì)發(fā)展而言,落實(shí)“以人為本,全面、協(xié)調(diào)、可持續(xù)的科學(xué)發(fā)展觀”的方方面面,更是集中表現(xiàn)為如何實(shí)現(xiàn)社會(huì)正義的問題。
近代以來,幾乎所有的思想家、政治家和社會(huì)大眾,都自覺不自覺地把解決社會(huì)正義及其實(shí)現(xiàn)的問題,訴諸制度設(shè)計(jì)安排的合理性問題。在現(xiàn)實(shí)中,自然會(huì)把社會(huì)不正義現(xiàn)象的根源直接歸咎于制度安排的問題,簡單地把爭取社會(huì)正義的現(xiàn)實(shí)途徑和中心任務(wù)僅僅希冀于制度設(shè)計(jì)安排的合理性、公正性。如果抽象地和歷史地講,這個(gè)觀念肯定是正確的,因?yàn)閺囊欢ㄒ饬x上說,人類爭取社會(huì)正義的歷史,就是社會(huì)的制度設(shè)計(jì)日趨合理的過程。
但不難發(fā)現(xiàn),僅僅訴諸制度維度來尋找實(shí)現(xiàn)社會(huì)正義的思路和方法,顯得一般化、抽象化。因?yàn)檫@會(huì)導(dǎo)致下面的問題:一是在同樣的制度設(shè)計(jì)下,社會(huì)正義的現(xiàn)實(shí)表現(xiàn)和實(shí)現(xiàn)程度為什么會(huì)存在極大的差距;二是在人類對于制度安排的程序正義(形式正義)的重視程度高于任何時(shí)代的當(dāng)下,為什么社會(huì)生活的每一個(gè)領(lǐng)域,無論是有關(guān)實(shí)質(zhì)正義還是有關(guān)形式正義的問題仍然有增無減。
諸如此類的問題使我們不得不對制度萬能論的立場和觀點(diǎn)產(chǎn)生懷疑。這種離開人以及人的道德意識(shí)的自覺,抽象、孤立地崇尚制度理性的思想傾向,無異于鼓吹沒有在場者的宏大歷史劇,自吹丟失靈魂理念的完美動(dòng)作藝術(shù)表演。事實(shí)上,制度設(shè)計(jì)安排與人及人的道德意識(shí)覺悟是決不能分離的,因?yàn)槿魏我环N形式上合理的制度安排,首先都既是人設(shè)計(jì)的,也是為人設(shè)計(jì)的,因而制度是人的思想理念的外化,它不可能脫離人和人的思想。從這個(gè)意義上說,再合理的科學(xué)制度,也不會(huì)超越人的思想的深刻性。其次,制度要通過人、依靠人來執(zhí)行,而人面對制度對其行為的規(guī)范的主觀心理認(rèn)同感,決定著其接受制度規(guī)范和執(zhí)行制度的情緒和意向行為。因而人的主觀意欲始終與制度的外在安排進(jìn)行著博弈。可見,合理的制度設(shè)計(jì)和安排,既是人的公共道德意識(shí)覺悟的結(jié)果,又是社會(huì)公共倫理的底線保障。同時(shí),制度的自覺維護(hù)和嚴(yán)格執(zhí)行,一定需要自覺道德意識(shí)的主體認(rèn)同。否則,即使一種制度設(shè)計(jì)得再合理,只要與個(gè)人的主觀意欲及個(gè)性價(jià)值訴求相抵觸,人就會(huì)盡可能去規(guī)避甚至踐踏這樣的制度安排,從而導(dǎo)致制度設(shè)計(jì)的公共性與人的行為動(dòng)機(jī)的私人性之間的矛盾加劇。對此,中國近代以來的主流觀點(diǎn)幾乎都試圖通過強(qiáng)調(diào)人的社會(huì)性,尤其是強(qiáng)調(diào)通過協(xié)調(diào)社會(huì)的物質(zhì)利益關(guān)系來解決這一矛盾的,然而事實(shí)是,如果人的主觀意欲沒有對秩序、正義、公平的心理認(rèn)同,這個(gè)矛盾就永遠(yuǎn)不可能真正得到解決。
對秩序、正義和公平的主觀認(rèn)同,既不能訴諸自發(fā)的原始意識(shí)(所以人性本善的先驗(yàn)唯心論的方法論理路是無效的),又不能訴諸自然理性、科學(xué)理性、工具理性等外在的他律性強(qiáng)制(所以制度萬能論和法律至上論的方法論理路也是無效的),而應(yīng)當(dāng)訴諸個(gè)體及交互主體性的道德自覺,即社會(huì)正義問題及其真正解決,與人性的自我覺悟以及交互主體性的道德理性共識(shí)密切相關(guān),用中國古話說,即與人的道德良知有關(guān)。因而即使在專制制度下,如果社會(huì)權(quán)力的控制者是一個(gè)明君,他照樣可以施行仁政,社會(huì)正義同樣能實(shí)現(xiàn)其最小傷害原則和最大兼容原則的統(tǒng)一。相反,即使在充分合理的民主制度下,如果社會(huì)的公共權(quán)力落在沒有道德底線的人手中,照樣會(huì)出現(xiàn)以眾暴寡,以所謂大多數(shù)人的價(jià)值偏好凌辱社會(huì)正義的真理性的現(xiàn)象。
可見,制度安排的合理性僅僅是相對而言的。惟其如此,我們就不難理解柏拉圖的《理想國》為什么要思考什么樣的制度才能確保社會(huì)的公共權(quán)力真正歸于優(yōu)秀的人(比如有高度道德自覺意識(shí)的哲學(xué)家),而不是重點(diǎn)討論哪種制度更合理。如果民主制度是盡善盡美的,那就不會(huì)有在民主的旗號(hào)下出現(xiàn)的那么多不正義的荒唐事了。一旦那些無德性的人騙取了選民或領(lǐng)導(dǎo)的信任,獲取了行使公共權(quán)利的主體資格,他們往往為了一己之私,既道貌岸然地大談公平正義,同時(shí)又巧言令色地捏造事實(shí)、混淆是非、擾亂視聽,把自己裝扮成社會(huì)正義的衛(wèi)道士而牟取個(gè)人名利。這比那些因無知少教而損益社會(huì)正義的行為更可怕。
片面理解和教條應(yīng)用西方現(xiàn)代性的制度理性思維,試圖用客觀理性的精神和方法研究人和人類社會(huì),以構(gòu)筑社會(huì)正義的客觀性原則的所謂科學(xué)方法,恰恰忽視了作為社會(huì)主體的人的特殊本性——心性及其理性自覺能力,特別是忽視了交互主體的道德共識(shí)對于實(shí)現(xiàn)社會(huì)正義的實(shí)質(zhì)意義。正是從這個(gè)意義上來說,我們不能簡單地把社會(huì)正義及其實(shí)現(xiàn)的問題的解決寄托在制度安排的合理性上。事實(shí)上,馬克斯•韋伯從宗教與形而上學(xué)的世界觀分離的角度出發(fā)所理解的現(xiàn)代性,也不是制度理性的單一維度,而是從客觀科學(xué)、普遍化道德與法律、審美的藝術(shù)方面這三大領(lǐng)域來規(guī)劃人類生活的結(jié)果,其中主體的道德意識(shí)的自覺具有更為實(shí)質(zhì)的地位和意義。
二、社會(huì)正義內(nèi)在地關(guān)涉人的道德意識(shí)
西方思想史上,早就有關(guān)于進(jìn)行人文社會(huì)學(xué)科研究,必須重視作為社會(huì)歷史主體的人及人性特殊性的論述。休謨曾經(jīng)說:“一切科學(xué),對于人性總是或多或少地有些關(guān)系,任何學(xué)科不論似乎與人性離得多遠(yuǎn),它們總是會(huì)通過這樣或那樣的途徑回到人性……哲學(xué)研究……是直搗這些科學(xué)的首都或心臟,即人性本身;一旦被掌握了人性以后,我們在其他各方面就有希望輕而易舉地取得勝利了。”[1]對于社會(huì)正義問題的認(rèn)識(shí)和實(shí)踐,更要直面人性。
盡管從道德理性的應(yīng)然價(jià)值希冀上看,人類所有文明實(shí)踐的共同思維目標(biāo)都在于追求社會(huì)公平正義,而且任何時(shí)代的制度安排,都以最大限度的實(shí)現(xiàn)社會(huì)公平正義為考量合理性的重要標(biāo)準(zhǔn)。但是,社會(huì)公平正義問題長期存在的重要原因之一仍然在于人性自身。正像我們要警惕口口聲聲高喊民主的人以民主的口號(hào)和外衣掩蓋自己大搞特權(quán)的實(shí)質(zhì)那樣,任何對公共理性的理念追求都是對人性本能的矯枉過正。民主的合理性恰恰在于,只有當(dāng)社會(huì)的公共選擇需要制度去解決時(shí),它才成為必要,因而這并不意味著它天生就是正當(dāng)?shù)摹R驗(yàn)樵跊]有道德意識(shí)共識(shí)、不協(xié)調(diào)的社會(huì)共同體中,如果完全按照合乎民主的完全一致或多數(shù)認(rèn)同原則辦事,那么,任何判斷和決策都是不可能的。不僅好事做不成,而且對于顯而易見的壞事也難以阻止。
與制度安排的合理性相比,道德意識(shí)的自覺和交互主體的公共倫理認(rèn)同處于更加根本的地位。正因?yàn)闄?quán)力容易使人的本性暴露,從而導(dǎo)致腐敗,所以任何政府和政黨都強(qiáng)調(diào)要廉潔奉公。但價(jià)值的應(yīng)然性判斷并不意味著事實(shí)的實(shí)然存在;否則,有了法的精神和理念就應(yīng)當(dāng)不會(huì)再有社會(huì)犯罪;有了對社會(huì)公平正義的思想追求,就不會(huì)再有不公平正義的事實(shí);有了廉潔奉公意識(shí),就不再有政府腐敗的現(xiàn)象……文化思想,特別是道德文化的任務(wù)就在于化人,在于讓人性的消極面自我縮小,而使其積極面充分彰顯。從這個(gè)意義上說,道德意識(shí)的自覺是人類極高的文化境界追求。
對于社會(huì)正義的最大傷害也源于人心的利己性。馬基雅維里認(rèn)為:“一切人都有惡的本性,只要一有機(jī)會(huì),人們就要按照這種本性來行事。”[2]所以,權(quán)力和腐敗天生就是孿生兄弟。因此有人“以獲取私人利益為目的濫用公共權(quán)利”參見世界銀行關(guān)于腐敗的定義,轉(zhuǎn)引自楊夏柏:《反腐敗研究(第六集)》,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9頁。,或者“因個(gè)人(個(gè)人的、家庭的、私人集團(tuán)的)金錢或地位上的利益而偏離公共職責(zé),或者是由于私人影響而違反權(quán)力行使規(guī)則的行為”參見約瑟夫•S•內(nèi)伊關(guān)于腐敗的定義,轉(zhuǎn)引自楊夏柏:《反腐敗研究(第六集)》,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60頁。。社會(huì)的腐敗現(xiàn)象,就像“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于外,腐敗不可食”在《漢書•食貨志上》中關(guān)于腐敗的原始陳述,意指谷物腐爛發(fā)霉。的自然現(xiàn)象一樣,是人的自然情欲本性的表現(xiàn)。
事實(shí)上,人們往往難以忘情于功名利祿,正如《管子•禁藏》所云:“夫凡人之情,見利莫能勿就,見害莫能勿避。其商人通賈,倍道兼行,夜以續(xù)日,千里而不遠(yuǎn)者,利在前也。”這是人的自然本性。馬克思一語道破天機(jī):“人們奮斗所爭取的一切,都同他們的利益有關(guān)。”[3]尤其是在霍布斯發(fā)現(xiàn)“第一是競爭,第二是猜疑,第三是榮譽(yù)”[4]三種造成人類爭斗的主要原因領(lǐng)域,這種自私“天性”表現(xiàn)得淋漓盡致。
當(dāng)我們超越了抽象人性論和先驗(yàn)人性論,回到現(xiàn)實(shí)中來考察人的思想、動(dòng)機(jī)及其行為時(shí),顯然必須承認(rèn)這一點(diǎn),因?yàn)椤叭说谋举|(zhì)并不是單個(gè)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xiàn)實(shí)性上,它是一切社會(huì)關(guān)系的總和”[5]。人“即使不像亞里士多德所說的那樣,天生是政治動(dòng)物,無論如何也天生是社會(huì)動(dòng)物”[6]363,“不管個(gè)人在主觀上怎樣超脫各種關(guān)系,他在社會(huì)意義上總是這些關(guān)系的產(chǎn)物”[6]12。
那么,社會(huì)的制度安排是如何利用和引導(dǎo)人的這一自然心性從而維護(hù)社會(huì)正義呢?對此,西方古典經(jīng)濟(jì)理論主張,通過競爭、通過人們之間公開的利益博弈就可以實(shí)現(xiàn)社會(huì)正義。但這種赤裸裸的私欲競爭,在理論上是以毫無個(gè)體差異的理性經(jīng)濟(jì)人為前提的。它在現(xiàn)實(shí)中無法詮釋不公平的馬太效應(yīng)。
事實(shí)上,就幾百年自由市場經(jīng)濟(jì)的激烈競爭而言,我們看到的不僅是其增進(jìn)人類福祉,而且無論是在經(jīng)濟(jì)領(lǐng)域還是在社會(huì)生活的其他領(lǐng)域,利用人的私欲的競爭,都在加劇著日益明顯的馬太效應(yīng)。這種把感官快樂與財(cái)富、道德的善和社會(huì)正義劃等號(hào)的做法,嚴(yán)格說來是一種偽善。因?yàn)樗斐傻纳鐣?huì)結(jié)果往往與其理論宣稱的預(yù)期大相徑庭。這就使我們不得不懷疑這種以自然人性論為基礎(chǔ)的功利主義的倫理思想的善惡主張,以及以此為基礎(chǔ)的古典自由主義的福利理論,究竟能否真正實(shí)現(xiàn)社會(huì)正義。
在傳統(tǒng)自由主義不能回避財(cái)富即是善的主張并不能真正解決社會(huì)正義問題時(shí),新自由主義就開始標(biāo)榜其“正義優(yōu)先于善”的主張。那么,這種觀點(diǎn)真的能夠解決社會(huì)正義問題嗎?只要看一下作為新自由主義的典型代表人物羅爾斯的理論尷尬就不會(huì)對此空懷希望了。羅爾斯給出的純粹形式正義的兩個(gè)原則分別是:“第一個(gè)原則:每個(gè)人對與所有人所擁有的最廣泛平等的基本自由體系兼容的類似自由體系都應(yīng)有一種平等的權(quán)利。”“第二個(gè)原則:社會(huì)和經(jīng)濟(jì)的不平等應(yīng)該這樣安排,使它們不僅在正義的儲(chǔ)蓄原則一致的情況下,適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差別原則),而且依系于在機(jī)會(huì)公平平等的條件下職務(wù)和地位向所有人開放(機(jī)會(huì)公平平等原則)。”[7]61羅爾斯認(rèn)為,在社會(huì)政治領(lǐng)域,“按照第一個(gè)原則,這些自由對于所有的人都應(yīng)該是一律平等的,因?yàn)橐粋€(gè)正義社會(huì)的所有公民都應(yīng)擁有相同的基本權(quán)利”[7]61。而第二個(gè)原則則適用于社會(huì)經(jīng)濟(jì)領(lǐng)域,它可以確保生產(chǎn)、交換、分配、消費(fèi)等的機(jī)會(huì)公平。在兩個(gè)原則的關(guān)系上,羅爾斯強(qiáng)調(diào)兩個(gè)優(yōu)先原則:第一個(gè)原則優(yōu)先于第二個(gè)原則;第二個(gè)原則中的公平的機(jī)會(huì)平等原則優(yōu)先于差別原則(第一個(gè)原則)。“這一次序意味著:對第一個(gè)原則所要求的平等的自由制度的違反不可能因較大的社會(huì)經(jīng)濟(jì)利益而得到辯護(hù)或補(bǔ)償。財(cái)富收入的分配及權(quán)力的等級制,必須同時(shí)符合平等公民的自由和機(jī)會(huì)的自由。”[7]62即是說,政治的平等自由優(yōu)先于經(jīng)濟(jì)的平等。尤其是第二個(gè)優(yōu)先原則,表面上看有克服功利主義的局限性的作用,特別是明確反對功利主義主張的苦樂之間可以等量置換,從而經(jīng)濟(jì)財(cái)富帶來的快樂足以撫慰政治和道德上的損失的非人道思想,主張無論如何,平等公民的自由和機(jī)會(huì)平等是無條件的,它決不會(huì)與經(jīng)濟(jì)利益進(jìn)行等量交換。這聽起來很有不為五斗米折腰的氣節(jié),但試想一想,假如一個(gè)連經(jīng)濟(jì)的平等交換權(quán)利都不能保障的社會(huì),人們還能奢望侈談?wù)纹降葐幔克裕伦杂芍髁x的正義觀也不過是一種白日做夢的癡心妄想而已。
康德倫理學(xué)的高明之處,在于發(fā)現(xiàn)了作為目的自身的人的道德行為不是來源于經(jīng)驗(yàn)和外在規(guī)范,而是我們對于先驗(yàn)的道德律令(“絕對命令”)的覺悟。“絕對命令”是經(jīng)驗(yàn)主體道德行為所依據(jù)的先驗(yàn)道德原則或規(guī)律。它遵循三條原則:其一是“不論做什么總應(yīng)該做到使你的意志所遵循的準(zhǔn)則永遠(yuǎn)同時(shí)能夠成為一條普遍的立法原理”[8]30;其二是“你的行動(dòng),要把你自己人身中的人性,和其他人身中的人性,在任何時(shí)候都同樣看作是目的,永遠(yuǎn)不能只看作手段”[9]81。也即應(yīng)該把人當(dāng)成目的;其三是“每個(gè)有理性東西的意志的觀念都是普遍立法意志的觀念”(即“意志自律”)[9]83。康德認(rèn)為,人只有以意志的先驗(yàn)道德律令指導(dǎo)其道德行為,才能體現(xiàn)善良意志,而不能僅僅按照自然人性的經(jīng)驗(yàn)感受去追求幸福。但是在經(jīng)驗(yàn)自我與先驗(yàn)自我發(fā)生矛盾(“德”與“福”的矛盾)時(shí),他就讓道德與幸福的完美結(jié)合的“至善”來解決這一矛盾。盡管一個(gè)人或一代人無法實(shí)現(xiàn)德福的統(tǒng)一而達(dá)到“至善”,只有世世代代的人(即整個(gè)人類)通過無止境的進(jìn)步才能不斷接近它,但是只要我們始終有這種以理性的愿望為基礎(chǔ)、追求理性的自我滿足的“至善”的道德意識(shí)的覺悟,包括社會(huì)正義在內(nèi)的“至善”目標(biāo)就不假外求了。
可見,無論如何那種以感性的自然人性為出發(fā)點(diǎn),先讓人人在經(jīng)驗(yàn)感受的快樂驅(qū)使下都變成自私勢利的小人,然后再想方設(shè)法用制度設(shè)計(jì)讓你回歸君子,實(shí)現(xiàn)社會(huì)公平正義的西方現(xiàn)代性理論,包括經(jīng)濟(jì)理性、政治理性和交往理性的諸多努力,在理論上都難自圓其說,實(shí)踐上都難以產(chǎn)生深遠(yuǎn)的現(xiàn)實(shí)效果。因?yàn)槿巳绻鄙倭苏x之公心,就會(huì)時(shí)刻算計(jì)如何使個(gè)人利益最大化。無論外在的制度安排多么科學(xué)合理甚至無懈可擊,只要人們誠心鉆營就會(huì)有隙可乘,而規(guī)避制度的懲罰則會(huì)成為他的平常心。
與之相反的是那些有誠信和正義之心的君子,則以自律的道德之心規(guī)范自己,處處循規(guī)蹈矩,即“君子懷刑”。至于有意鉆營制度的空隙,對他們而言則是不可思議的事情。如果有人敢越雷池一步,必被視作寡廉鮮恥。可見,正義發(fā)自內(nèi)在心性,而不是來自外在規(guī)范。中國古代的儒家智慧的深刻之處,就在于參透了這一點(diǎn),《大學(xué)》有云:“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身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格物而后致知。致知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10]
三、傳統(tǒng)道德理性與社會(huì)正義的關(guān)系
在新的歷史時(shí)期,以主體修養(yǎng)、內(nèi)心體驗(yàn)和道德實(shí)踐為核心的中國古代思想文化,特別是儒家的道德理性思維,對于科學(xué)地呈現(xiàn)和真正地實(shí)現(xiàn)社會(huì)正義,具有歷久彌新的積極價(jià)值。
在經(jīng)濟(jì)全球化的趨勢日益加劇、政治多極化的格局已經(jīng)形成、文化多元化的態(tài)勢不可避免、信息技術(shù)網(wǎng)絡(luò)化的工具理性手段日益彰顯的當(dāng)下時(shí)代,如何將現(xiàn)代性內(nèi)化為一種主體生命的意義?猶如伽達(dá)默爾所說:體驗(yàn)作為生命的經(jīng)歷,“它以兩個(gè)方面的意義為根據(jù)的:一方面是直接性,這種直接性先于所有解釋、處理或傳達(dá)而存在,并且只是為解釋提供線索、為創(chuàng)作提供素材;另一方面是由直接性中獲得的收獲,即直接性留存下來的結(jié)果”[11]。中國傳統(tǒng)哲學(xué)的心性義理之學(xué),為我們提供了這種主體體認(rèn)思維的獨(dú)特智慧,其直覺智慧啟迪我們,面對當(dāng)下全球化的境遇,我們必須在和而不同的原則下,學(xué)會(huì)整合創(chuàng)新的全球思維;反對傳統(tǒng)形而上學(xué)教條下的兩種極端思維傾向:其一是文化一元論的話語霸權(quán)主義思維;其二是文化相對主義的消解理性的所謂后現(xiàn)代主義思維。前者根據(jù)西方現(xiàn)代性的理性至上原則兜售西方的制度理性,主張這種制度理性能夠公平分配一切社會(huì)資源、財(cái)富和權(quán)利,從而實(shí)現(xiàn)社會(huì)正義;后者則在價(jià)值多元的旗號(hào)下,主張?jiān)趺礃佣夹校瑥亩磳ξ幕臏贤ㄅc融合、主張社會(huì)正義并無客觀標(biāo)準(zhǔn)。
相形之下,中國古代的思想智慧則以主體內(nèi)在生命體驗(yàn)的方式,早熟性地覺悟到人生智慧,為社會(huì)正義及其實(shí)現(xiàn),找到了內(nèi)在的文化本體論根據(jù)。因?yàn)槲幕壠鹩谌嘶幕墓δ茉谟诨恕V袊糯枷胫腔郏貏e是儒家思想的人生智慧,從內(nèi)在心性的道德悟性層面,詮釋人的外在行為及社會(huì)義理的合理性根據(jù)的思想方法,對于現(xiàn)時(shí)代人們真正實(shí)現(xiàn)社會(huì)正義,無疑仍然具有重要的積極意義。
“中國文化在開端處的著眼點(diǎn)是在生命,由于重視生命、關(guān)系生命,所以重德。”[12]人對于自身德性的認(rèn)識(shí)并不像認(rèn)識(shí)外界自然那樣,需要不斷積累見聞,而是訴諸直覺悟性的慧根,所以北宋張載云:“德性之知不萌于見聞”,主張宇宙大道就在日常倫用中,所以“天道遠(yuǎn),人道邇”。因此,對于人生和社會(huì)智慧的覺悟并不必然依賴于知識(shí)的多寡。正是從這個(gè)意義上來說,中國先哲的人生智慧的早熟,正是在天人關(guān)系緊張、人之對天無知而敬畏的狀況下,人類對于自身心性和德行的內(nèi)省的結(jié)果。這些先哲主張以德配天,替天行道,追求天人合一;而人只要有了體道、知道的主體覺悟,行道、布道、守道的實(shí)踐行為就自然言行化成了。正可謂:“朝聞道,夕死可矣!”
從這個(gè)意義上來說,全部中國思想史是一部主體體認(rèn)人生之道、社會(huì)正義之道、宇宙大道的悟道的覺悟史。如《尚書•洪范》中所說的“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cè),王道正直”。可見,古人把正確的政令、規(guī)范和法度視作人君對于天道的覺悟。
《左傳》中“臣聞小之能敵大也,小道大淫。所謂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和“王祿盡矣,盈而蕩,天之道也”的立論,更有悟道、持道、守道的主體覺悟的意境。
老子認(rèn)為,對于作為宇宙的本原和普遍規(guī)律的道的認(rèn)識(shí),必須訴諸直覺悟性。在老子以前,人們對生成萬物的根源只推論到天,而沒有涉及天究竟還有沒有根源。到了老子,開始推論天的來源,于是提出了道。道雖存在于萬物之中,但不同于可感覺的具體事物,它是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搏之不得的,是構(gòu)成天地萬物的共同本質(zhì)的東西。所以,只有富有道德大心慧根的人才能覺悟它,即“無思無慮則知道”。
戰(zhàn)國時(shí)期,齊國稷下道家“精氣”說,把虛而無形的道看作是流布于天地之間、遍存于萬物內(nèi)部的“精氣”。《管子•內(nèi)業(yè)》認(rèn)為,“凡道,無根無莖,無葉無榮。萬物以生,萬物以成,命之曰道。精也者,氣之精者也。氣道乃生。”人何以體道,貴在采天地萬物之氣而內(nèi)化為道德之氣。
韓非汲取并發(fā)展了老子的樸素辯證法,提出關(guān)于道、德、理三者相互關(guān)系的學(xué)說,他說:“道者萬物之始,……萬物之源”,是“萬物之所然”、“萬物之所以成”,是萬物的普遍規(guī)律,而萬物的特殊規(guī)律就是“理”,道是“萬物之所稽”,“萬物各異理而道盡稽萬物之理”。而只有人的德性,才能達(dá)理而體道。
《荀子•天論篇》強(qiáng)調(diào),“天道有常,不以堯存,不以桀亡”。人們必須替天行道,以德感天,而不能怨天尤人。在中國哲學(xué)的“天人合一”的觀念看來,在天之道與為人之道是一致的,人道是由天命決定的。論道做人,就是知天命的功夫。在商周時(shí)代,天就被人們在心中肯定為至高無上的神,它具有降臨人世“吉兇禍福”、“得失成敗”的權(quán)威。《中庸》更提出了“天命之謂性”的命題,一方面用天命來說明人的本性,另一方面用人性來說明天之所命,這是把天內(nèi)在化了,于是就自然引出了“天人合一”的理想。所謂“天人合一”就是發(fā)揮人的本性,以便與天的潛能合而為一,道家創(chuàng)造性地把天的范疇發(fā)展到道的范疇,使儒家的先王之道、君子之道發(fā)展成為一種本體之道、宇宙之道。盡管它認(rèn)為道是一切現(xiàn)象的根源和最終歸宿,是自然化生的過程和全體宇宙的本質(zhì),道包含并遵循“有無相生”、“負(fù)陰抱陽”、“無為而無不為”,反、覆、一的辯證法則,但最終還是要落到道可為人用來處世治國上,故道不遠(yuǎn)人,人能弘道。這與儒家強(qiáng)調(diào)的學(xué)問和人生履踐的全部功夫都在于論道、行道、弘道是一致的。特別是中國古典文化的人本主義精神,使其對于道之本體的理解側(cè)重人倫綱常,所以論道的關(guān)鍵仍然回到了守常做人。
這種著眼于生命道德的人生智慧,以敬天愛民的道德實(shí)踐為出發(fā)點(diǎn),覺悟到“性命天道相貫通”的直覺悟性的體道途徑的重要性,把主體的德性覺悟,視作體天道、知事理、順人心的先決條件。故此必先說“正德”,然后才可說“利用”與“厚生”。即是說,只有內(nèi)在心性的德性實(shí)踐的功夫到位了,外在的政治實(shí)踐的理想才有可能實(shí)現(xiàn)。對于社會(huì)正義而言,先有了正義之心性覺悟的內(nèi)在意識(shí),之后才有社會(huì)正義的行為努力和制度安排。如儒家正視道德人格的生命,強(qiáng)調(diào)使生命“行之乎仁義之途”,從而以精神生命的涵養(yǎng)來控制情欲生命,以悲憫之情追求最高的道德價(jià)值。“致中和”就是為了使“天地位”,使“萬物育”。這里的“位”可以理解為有差異的正義秩序,它是確保發(fā)展(“育”)的重要前提。
自西周以降,中國傳統(tǒng)思想往往“以倫常治道的人生智慧為惟一關(guān)心的問題,而無暇論究好像不著實(shí)際,不合實(shí)用的希臘智者所醉心的宇宙根源問題,以及認(rèn)識(shí)自然與一般知識(shí)技能問題”[13]。這種輕自然、重倫常,反天道、重人道的社會(huì)思潮,在春秋時(shí)展為一種普遍的時(shí)代精神。如《左傳•昭公十八年》中子產(chǎn)所云:“天道遠(yuǎn),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天道是彼岸世界的事,不可及亦不可知,即莊子所說的“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論”。人際關(guān)系則現(xiàn)實(shí)得多,于是便成為人們注視的中心。人們以往在將其與西學(xué)近世以來的科學(xué)理性思維的比較中,這種道德理性的思維大凡都受到批判和否定。但是,今天看來,這種重視人的道德良知的古代思想智慧,對于社會(huì)正義及其積極實(shí)踐,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積極價(jià)值。這一點(diǎn)已被大量的歷史事實(shí)所證明。
例如,在公元5—15世紀(jì),中國傳統(tǒng)重視人的道德理性覺悟的思維方式的積極作用就得到了充分地發(fā)揮。這一時(shí)期,中國封建社會(huì)走向鼎盛、東方文明呈現(xiàn)燦爛輝煌,中國社會(huì)的物質(zhì)文明和道德文明相得益彰,實(shí)用道德理性的思維方式對此功不可沒。
首先,就思維的廣度而言,當(dāng)時(shí)中國人充分地涉及了自然、人文、社會(huì)、技術(shù)、藝術(shù)、建筑、音樂等領(lǐng)域,而不像中世紀(jì)西方人那樣“只知道一種意識(shí)形態(tài),即宗教和神學(xué)”。明代出版的百科全書——《永樂大典》就充分體現(xiàn)了這種思維廣度,它涉及自然、社會(huì)、律法、藝術(shù)、哲學(xué)、工藝等各個(gè)方面的內(nèi)容。對此,著名的科學(xué)史學(xué)家李約瑟博士曾評價(jià)說:“中國的這些發(fā)明和發(fā)現(xiàn)遠(yuǎn)遠(yuǎn)超過同時(shí)代的歐洲,特別是在15世紀(jì)以前更是如此(關(guān)于這一點(diǎn)可以毫不費(fèi)力地加以證明)。”參見李約瑟著《中國科技史》序言(科學(xué)出版社1975年版)。
其次,從思維方法來說,這個(gè)時(shí)期的中國人通過強(qiáng)調(diào)實(shí)用,把道德理性的思維趨向發(fā)展為重視技藝、生產(chǎn)和應(yīng)用價(jià)值的實(shí)證性方法,因此決定了對經(jīng)驗(yàn)方法的迷戀。而西方中世紀(jì)則獨(dú)尊神學(xué)理性的抽象方法,追求和思考那些虛無縹緲的、跨越時(shí)空關(guān)系難以直接體驗(yàn)的神學(xué)問題,并以主觀繁瑣的三段論進(jìn)行證明。
再次,從思維結(jié)果看,這一時(shí)期中國人的思維方式成功地完成了以火藥、羅盤針、印刷術(shù)為代表的重大發(fā)明,從而使其在天文、地理、算術(shù)、歷法、醫(yī)學(xué)、農(nóng)業(yè)、水利、冶金諸方面都雄踞世界前列。而中世紀(jì)西方人的神學(xué)思維方式恰如培根所說,是“不生育的尼姑”,沒有在科技方面結(jié)出思想果實(shí)。這一時(shí)期,中國思維以博大而精深的體系君臨世界文明之林。仰觀天文,俯察地理,遠(yuǎn)取諸物,近求諸身,統(tǒng)攝天下萬物萬事于思維之中,并對其予以深刻的反思。在哲學(xué)理論思維上,形成了諸多體系和不同理論,既有宋明程朱、陸王的理學(xué)心學(xué)體系,又有張載、陳亮、葉適等的唯物主義思想。無論在本體論、認(rèn)識(shí)論還是辯證法方面,都是歐洲中世紀(jì)哲學(xué)思維所不能比擬的。
今天,人心問題仍然比制度問題更為重要,而且仍然是制度問題的前提條件,社會(huì)正義及其實(shí)現(xiàn)也不例外。人們只有廣泛地達(dá)到了對社會(huì)正義的道德意識(shí)自覺,社會(huì)正義的制度規(guī)范才能真正發(fā)揮作用。所以,在社會(huì)正義及其實(shí)現(xiàn)的問題上,既不可完全訴諸西方現(xiàn)代性的制度理性安排,而對中國傳統(tǒng)道德理性文化資源采取“丟盡自家無覓處,手捧金缽效貧兒”盛唐詩人司空徒詩句。的本土文化虛無主義態(tài)度,也不能完全希冀中國傳統(tǒng)心性義理的德性文化能徹底解決現(xiàn)代社會(huì)的正義問題,而應(yīng)以融會(huì)中西、整合古今的創(chuàng)新思維,讓社會(huì)正義通過人的道德意識(shí)自覺與合理的制度規(guī)范相得益彰而蔚然成風(fēng)。
四、德性與制度理性的結(jié)合
在現(xiàn)代化的發(fā)展理路,以及現(xiàn)代社會(huì)正義的實(shí)現(xiàn)途徑,尤其是在現(xiàn)代企業(yè)的管理模式上,自上個(gè)世紀(jì)80年代以降,世界范圍內(nèi)出現(xiàn)了一個(gè)不爭的奇怪現(xiàn)象,即中國人向美國人學(xué)習(xí),美國人向日本人學(xué)習(xí),而日本人則向中國古代人學(xué)習(xí)。這一現(xiàn)象的重要現(xiàn)實(shí)基礎(chǔ)是歷史上深受儒學(xué)德性思維影響的日本、韓國、新加坡等國家和地區(qū),戰(zhàn)后經(jīng)濟(jì)的突飛猛進(jìn),以及社會(huì)正義的有益增進(jìn)。其重要的原因在于這些國家和地區(qū),在現(xiàn)代社會(huì)的發(fā)展和正義實(shí)現(xiàn)的理念上,很好地協(xié)調(diào)了西方制度理性與東方道德理性的關(guān)系,特別重視發(fā)揮儒家倫理重視道德意識(shí)自覺的積極作用。猶如美國環(huán)太平洋研究所所長弗蘭克•吉伯尼在其《設(shè)計(jì)的奇跡》中所指出的,許多世紀(jì)以來古老的儒家勞動(dòng)道德傳統(tǒng)是日本成功的決定性因素之一。因而他提出日本是“儒家資本主義”,以區(qū)別于西方資本主義。日本森島道雄教授1975年在倫敦經(jīng)濟(jì)學(xué)院講學(xué)時(shí)曾經(jīng)說:“儒家學(xué)說不鼓勵(lì)個(gè)人主義。它在性質(zhì)上是理智合乎理性的,它摒棄其它宗教所共有的那種神秘主義和妖術(shù)咒語。日本人在明治維新之后非常迅速地消化西方技術(shù)和科學(xué)的能力,至少應(yīng)部分地歸功于儒家學(xué)說的教育。”日本企業(yè)家澀澤經(jīng)常把《論語》抄本帶在身邊,他覺得企業(yè)需要有強(qiáng)調(diào)協(xié)調(diào)人們之間相互關(guān)系的儒家思想,以免僅僅強(qiáng)調(diào)經(jīng)濟(jì)理性而墮落為鉆營私利。他的目標(biāo)是“把現(xiàn)代企業(yè)建立在算盤和《論語》的基礎(chǔ)上”。
第一,傳統(tǒng)儒學(xué)的道德理性思維的人本精神,從主體性的根本上規(guī)定著社會(huì)正義的價(jià)值目的。
儒家的人本精神、無神論思想以及和合文化心理等,無疑在現(xiàn)代社會(huì)正義實(shí)現(xiàn)的過程中,都具有重要的意義。盡管以往人們已從許多方面論述了儒家文化與現(xiàn)代性的矛盾對立,例如有人認(rèn)為儒家的思維水平和思維結(jié)構(gòu)與現(xiàn)代科學(xué)發(fā)展不相適應(yīng),儒家的價(jià)值系統(tǒng)與現(xiàn)代的商品意識(shí)、競爭機(jī)制不相適應(yīng),儒家的綱常名教與現(xiàn)代的民主、法制不相適應(yīng)等,但是在當(dāng)今激烈競爭的社會(huì)里,儒家重視人的價(jià)值、作用的主體道德意識(shí)和人文精神的思想,無疑對于道德淪喪和人性異化是一種校正。“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制天命而用之”,等等,都強(qiáng)調(diào)人生價(jià)值和人的道德主體精神,它從根本上強(qiáng)調(diào),人是目的,用康德的話說,人是目的本身。一切制度安排和理念追求及行為過程,其效用的評價(jià)的標(biāo)準(zhǔn)都是人,社會(huì)正義的主張和實(shí)現(xiàn)途徑也不例外。所以無論是發(fā)展生產(chǎn)、提高效率、增進(jìn)福利的正義實(shí)現(xiàn)途徑,還是利益博弈的經(jīng)濟(jì)理性主張,甚至商談倫理的交互主體性共識(shí)的后現(xiàn)代正義理路,歸根結(jié)底,都不能離開人的道德理性的健康發(fā)展的評價(jià)標(biāo)準(zhǔn)。
第二,儒學(xué)“中和位育”的思維方式,是我們正確理解和對待社會(huì)正義的重要思想方法基礎(chǔ)。
儒家強(qiáng)調(diào)“中庸”,即承認(rèn)事物的矛盾(“過”和“不及”),但又主張“無過”、“無不及”,強(qiáng)調(diào)“中和”、“中道”、“和而不同”,即主張矛盾的統(tǒng)一。它不僅是一種道德規(guī)范,而且是具有辯證思想的觀察世界和處理問題的根本原則和思想方法。這一思想,在處理人際關(guān)系上,主張“和為貴”,提倡“謙讓”作風(fēng),強(qiáng)調(diào)建立和諧的人際關(guān)系。在處理民族國家關(guān)系上,主張“合二而一”,提倡整體觀念,強(qiáng)調(diào)安定和統(tǒng)一。但是,“和”是以承認(rèn)差異和不同為前提,不同是生生不息的先決條件。這即是公元前7世紀(jì)史伯在《國語•鄭語》中強(qiáng)調(diào)的“和實(shí)生物,同則不繼”的思想。所以,猶如和諧是多元共生一樣,正義也不是絕對平均、完全平等,而是存在差異和區(qū)別的相對公平。
事實(shí)上,“二戰(zhàn)”后日本經(jīng)濟(jì)奇跡的出現(xiàn),既受激烈競爭的西方文化思想的影響,也有儒家重感化、重和諧觀念的影響。“和”是“和為貴”的儒家思想和“大和”日本文化的結(jié)合,它對內(nèi)要求企業(yè)主與工人、工人與工人之間的和諧,對外要求在企業(yè)之間,政府、工會(huì)、資方之間的和諧,互相信任,創(chuàng)造一種融洽的氣氛,而非西方那種由權(quán)利和義務(wù)所規(guī)定的非情感化的氣氛。
第三,傳統(tǒng)道德理性思想與現(xiàn)代制度理性的融合,可以協(xié)調(diào)現(xiàn)代社會(huì)正義中的義理關(guān)系。
事實(shí)上,儒家的義利觀在當(dāng)代資本主義發(fā)展中,特別是在東亞經(jīng)濟(jì)發(fā)展中,對于社會(huì)正義的實(shí)現(xiàn),發(fā)揮了重要的調(diào)節(jié)作用。中國的傳統(tǒng)儒家強(qiáng)調(diào)“見利思義”,當(dāng)義利相沖突時(shí),主張應(yīng)取“義”而舍棄“利”,“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孔子這種輕視富貴和功利的思想,到了孟子,變成了“義”“利”完全脫節(jié)的倫理觀,他說:“何必曰利”。這種輕視功利的意識(shí),在日本則被改造成為“仁”與“富”結(jié)合的經(jīng)營管理思想。
日本著名的實(shí)業(yè)家,創(chuàng)辦了五百多個(gè)大企業(yè)并被譽(yù)為“日本資本主義之父”的澀澤榮一,不但在實(shí)踐中應(yīng)用儒家思想,而且著有《論語與算盤》、《論語講義》等書,闡述他的儒家資本主義精神。他的倫理信念是《論語》與算盤合一,他的口號(hào)是“仁與富可能也必須并存”。他不但把儒家的仁、義、禮、智、信這“五常”作為指導(dǎo)思想,而且還把“五德”,即智、信、仁、勇、嚴(yán)這些兵家的思想,作為自己經(jīng)營管理的準(zhǔn)則。他甚至把儒家的義利矛盾觀解釋為義利統(tǒng)一觀。在解釋為什么企業(yè)要同儒家道德相結(jié)合時(shí),他曾直言不諱地說,道德和經(jīng)濟(jì)本來是并行不悖的,然而,由于人們常常傾向于見利而忘義,所以古代圣賢極力糾正這一弊病,一面積極提倡道德,一面又警告非法牟利的人們,后來的學(xué)者誤解了孔夫子的真正思想,忘記了高產(chǎn)乃為善之道。他明確主張,只有義理統(tǒng)一,才能真正實(shí)現(xiàn)社會(huì)正義。
第四,儒學(xué)思維重群體道德理性覺悟的思想,對于現(xiàn)代公民社會(huì)強(qiáng)調(diào)通過“積極參與”增進(jìn)社會(huì)正義的途徑的思想很有啟迪。
戰(zhàn)后日本經(jīng)濟(jì)的發(fā)展和社會(huì)正義的進(jìn)步,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重視了儒家的整體化和團(tuán)體意識(shí)的作用。事實(shí)上,戰(zhàn)后日本經(jīng)濟(jì)的恢復(fù)和發(fā)展,儒家的整體化和集團(tuán)意識(shí)不僅沒有導(dǎo)致壓抑現(xiàn)代社會(huì)民主正義,而且恰恰相反,這種重群體團(tuán)隊(duì)意識(shí)的儒家倫理思想倒成了日本現(xiàn)代社會(huì)經(jīng)濟(jì)和正義發(fā)展進(jìn)步的堅(jiān)實(shí)思想基礎(chǔ)。由于儒家倫理的群體意識(shí)強(qiáng)調(diào)效忠和集體主義,個(gè)人主義就受到了限制,而個(gè)人主義淡薄可能是日本隨后實(shí)現(xiàn)現(xiàn)代化的獨(dú)特的有利條件。日本人的集體主義,是實(shí)業(yè)家和勞動(dòng)者互相依賴所表現(xiàn)出來的一種儒家倫理色彩。表面上看來,這種集體意識(shí)似乎不為個(gè)人提供超越別人的刺激,然而,這種集體意識(shí)卻為日本經(jīng)濟(jì)帶來成功。對此,弗蘭克•吉布尼在《日本經(jīng)濟(jì)奇跡的奧秘》一書中,從宗教文化學(xué)的角度,指出這是日本將古老的儒家倫理與戰(zhàn)后由美國引入的現(xiàn)代經(jīng)濟(jì)民主主義兩者糅合在一起,并加以巧妙運(yùn)用的結(jié)果。
儒學(xué)重視人的道德理性覺悟?qū)τ诂F(xiàn)代社會(huì)正義實(shí)現(xiàn)的積極意義,以東亞社會(huì)迅速崛起的歷史事實(shí),向僅僅訴諸提高生產(chǎn)效率從而增加社會(huì)物質(zhì)財(cái)富來實(shí)現(xiàn)社會(huì)正義的傳統(tǒng)歐洲中心主義文化模式提出了挑戰(zhàn)。今天,在堅(jiān)持以法治國,建設(shè)社會(huì)主義法制國家,走制度理性優(yōu)先的現(xiàn)代性社會(huì)正義道路,實(shí)現(xiàn)社會(huì)和諧的過程中,弘揚(yáng)和彰顯傳統(tǒng)儒學(xué)道德理性的思想資源,讓其與制度理性相得益彰,無疑是實(shí)現(xiàn)社會(huì)正義的明智的文化決斷。
[參考文獻(xiàn)]
[1]休謨.人性論(上)[M].關(guān)文運(yùn),譯.北京:商務(wù)印書館,1982:6-7.
[2]馬基雅維里.君主論[M].潘漢典,譯.北京:商務(wù)印書館,1985:80.
[3]馬克思.第六屆萊茵省議會(huì)的辯論[M]∥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82.
[4]霍布斯.利維坦[M].黎思復(fù)等,譯.北京:商務(wù)印書館,1985:94.
[5]馬克思.關(guān)于費(fèi)爾巴哈的提綱[M]∥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8.
[6]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M]∥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8.
[7]約翰•羅爾斯.正義論[M].何懷宏等,譯.北京:中國社會(huì)科學(xué)出版社,1988.
[8]康德.實(shí)踐理性批判[M].關(guān)文運(yùn),譯.北京:商務(wù)印書館,1960:30.
[9]康德.道德形而上學(xué)原理[M].苗力田,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10]朱熹.四書集注[M].長沙:岳麓書社,2000.
[11]伽達(dá)默爾.真理與方法[M].洪漢鼎,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9:78.
[12]牟宗三.中國哲學(xué)十九講[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43.
[13]侯外廬.中國思想通史: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23.
文檔上傳者
相關(guān)推薦
社會(huì)變遷論文 社會(huì)藝術(shù) 社會(huì)文化 社會(huì)保障 社會(huì)學(xué) 社會(huì)安全論文 社會(huì)治安 社會(huì)研究 社會(huì)轉(zhuǎn)型 社會(huì)主義建設(shè) 紀(jì)律教育問題 新時(shí)代教育價(jià)值觀
- 主導(dǎo)社會(huì)服務(wù)社會(huì)
- 社會(huì)政策
- 社會(huì)政策
- 社會(huì)公正社會(huì)主義遺產(chǎn)和社會(huì)民主主義
- 社會(huì)主義現(xiàn)象和社會(huì)主義本質(zhì)
- 和諧社會(huì)與社會(huì)學(xué)
- 社會(huì)主義社會(huì)矛盾失誤
- 社會(huì)公正和社會(huì)穩(wěn)定
- 社會(huì)主義社會(huì)矛盾
- 和諧社會(huì)增強(qiáng)社會(huì)活力思考